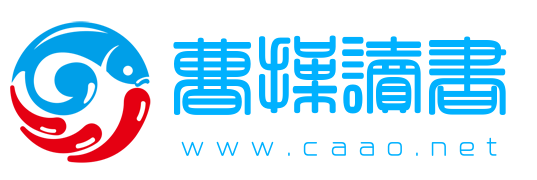浮图塔
书籍简介

内容简介
<span style="color:#7f7f7f">晋江榜推高积分vip2014.04.22完结,总书评数11618 当前被收藏数9451</span>没有温暖的心,却有世上最动人的眼睛。他是恶鬼,也是佛陀......<span style="color: #6f6f6f">第1章惊塞雁</span>隆化十一年春天,下了很长时间的雨。都城被浸泡在
内容在线试读
本图书由(零点小飞侠)为您整理制作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及出版图书,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浮图塔》
作者:尤四姐
第1章 惊塞雁
隆化十一年春天,下了很长时间的雨。都城被浸泡在水气里,约摸有四十来天没有见到太阳了。
江山风雨飘摇,一切都岌岌可危。高卧龙床的元贞皇帝病势每况愈下,中晌听说已经停了饮食,也许再过不久就要改年号了。
谁做皇帝,对于乾西五所的宫眷来说并不重要。女人眼皮子浅,不似朝中大臣心怀天下,她们只知道自己进宫不过月余,卑微的封号才刚定不久,接下来迎接她们的不是帝幸,不是荣宠,也许是庵堂里的青灯古佛、皇陵里的落日垂杨、地宫里冰冷潮湿的墓墙……
谁知道呢!
“早料到有今日,当初就不该进宫来。”一个选侍站在檐下呜咽,“皇上正值壮年,谁知……竟是个没寿元的。”
“这种事何尝轮到咱们自己做主?”另一个捂住她的嘴左右观望,压着嗓子道,“你小声些儿,叫人听见了,咱们只怕捱不到最后,倒要先行一步了。”
“如今还怕什么,只求老天开眼,保吾皇万寿无疆,让咱们多活两年,便是上辈子积德行善的福报了。”
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后宫的女人何尝不是这样。既进了宫,万事系在皇帝一身。君王体健,她们不说何等优渥自在,至少性命尚且无虞;君王身死,膝下有子女的可以退归太妃位,至于那些无所出的、位分低微的,娘家再没个倚仗,似乎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了。
这庞大的、千疮百孔的帝国,落到谁手里,都是个无法转圜的死局。大邺开国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四年了,这二百多年里经历过辉煌,也出过英主。彼时开疆拓土,迁都京师,令八方来朝,四海称臣,盛世繁华,历朝历代无一能及。然而国运也有轮回,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渐渐老迈,拖着臃肿的身躯,反应迟钝,接下来如何,没人说得清。
音楼把直棂窗阖上,转身到桌前沏茶。青花瓷杯里注进茶汤,高碎的残沫儿在沸水里上下翻滚。
“喝茶。”她往前推了推,“雀舌的沫子也比针螺要好,我老家产茶,进了宫,反倒连个茶叶的边儿都摸不着了。以前片子里头还要挑嫩尖,现在只有喝零料的份儿了,可怜。”
她总是这样,天大的事与她都不相干似的,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就连在她肩头刺花,她也是笑着的。李美人没她那么好的兴致,隔开杯盏蹙眉叹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品茶!”
什么时候?大约是死到临头了。她也忐忑,但是又能怎么样!她坐下来,拿盖儿刮了刮浮沫,慢慢道:“咱们这些人是笼中鸟,进了宫,生死早就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了。不过活了一天,算两个半天。等旨意颁了,往后怎么着,看各自的造化吧!”
李美人沉默下来,愣眼看了她半天才道:“怪我多事,现在想想,当初你要是被撵出去,也就不必操今天这份心了。”
音楼听了笑道:“撵出去了日子是好过的么?说不定还不及现在。弟兄不待见,将来嫁人,也别指望能配好人家。没出息的傻丫头,保个姨娘的媒就不错了,还能蹿到天上去?其实现在也不必太过忧虑,太医院那些医正都有手段,兴许研制出什么方子来,一下儿就把万岁爷的病治好了。”
这么开解一番,倒也略感宽怀。虽然皇帝的病拖了两年不见起色,毕竟还没咽气。像以往死过去好几回,不也救回来了吗,这次一定还有这样的造化。鬼门关转一圈,权当下江南了。
至于音楼和李美人的交情,原有一说。她们同批进宫,譬如乡里赴考的生员,要是论起来,也能称作同年。一道进宫门,一间屋子里验了发肤手足,到了验身那一关,自己闹了个笑话,是李美人帮她解的围。
参选的良家子,首先头一条就要保证清白。宫里太监缺德,以前曾有过坑害姑娘的事,后来尚宫局为保万无一失,不知怎么想出个妙方儿来——簸箕里铺好面粉放在炕头,令参选者蹲踞在上,给你嗅胡椒面儿,呛了总要打喷嚏吧?这一发力就看出来了。据说处子身下纹丝不动,要是破了身的……大概就当风扬其灰了。这是进宫后才知道的秘闻,以前从没有听说过。她那时候傻,尚宫命她上炕对准面粉,她是对准了,只不过是用脸。结果喷嚏直射进簸箕,把尚宫喷了个满身满头。瞧她这股子笨劲儿,脑子不灵便不能进宫听差,就算勉强留下,也是个不起眼的淑人。幸亏李美人仗义,替她说尽了好话,她才没被遣返原籍。不想阴差阳错,居然挣了个才人。
当然了,才人还是个喝高碎的才人,依旧上不了台面。不过不用进浣衣局做工,且有时间春花秋月,已经是人生一大乐事了。她没想过承雨露之恩,皇帝缠绵病榻,后宫早就形同虚设。只是这样的境况,仍旧三年一大选,里头打的什么算盘,细想令人胆寒。
一阵风吹来,槛窗不知怎么开了,绵密的雨飒飒落在书页上,把案头淋得尽湿。李美人起身拨木栓,突然回过头问她,“你说我们会不会充为朝天女?”
音楼打了个寒战,这种事心知肚明,何必说出来!
朝天女的来由,简而言之就是拿活人殉葬。大邺建国那么多年,这条陋习从来没有废除过。她们这些人,在当权者眼里还不如蝼蚁。皇帝是这泱泱华夏的主宰,是所有人的天。活着的时候享尽荣华富贵,死了也要带一帮人下去伺候。皇帝一旦停床,内官监的太监就准备拟名单了。这是公报私仇的好机会,大臣们纷纷开始行动,朝堂之上不能肃清政敌,就设法算计对方的女儿,弄死一个是一个。不过死也不是白死,丧家从此有了特定的称谓,叫“朝天女户”。这种荣耀世袭罔替,下一任皇帝会对其家人给予优恤,以表彰她们的“委身蹈义”。
究竟死与不死,没人说得准,得看运气。音楼放下茶盏道:“如果命大,出家或是守陵,还能有一线生机。”
李美人缓缓摇头,“只怕轮不着咱们,太祖皇帝驾崩,殉葬者一百二十人之众。成宗皇帝少些,也有四十余人。后来的皇帝多则七八十,少则五六十,到如今成了惯例。你算算,乾西五所里有多少人?加上那些御幸却未有子女的,加起来恰好够数了。”
够数了,一个也别想逃。朝天女的人数无定员,一般是往多了添,没有削减的道理。她抬眼看檐外飞雨,鼻子有些发酸,“我们倒罢了,承过幸的妃嫔也逃不脱,真是可悲。”
“你还有心思同情别人么?咱们守着清白身子殉葬,细想起来谁更可悲?”李美人抚抚褙子上的摘枝团花,缓步踱到门前,“音楼,眼下能救咱们的,只有司礼监的那帮阉竖了。”
说起司礼监,足以叫人闻风丧胆。当初成宗皇帝重用宦官挟制朝中大臣,无非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谁知后世帝王效仿之余发扬光大,到现在成立了缉事衙门,提督太监甚至代皇帝批红,一手把持朝政。像这种嫔妃殉葬的事,自然也在司礼监的管辖范围之内。
音楼怔怔望着她,“你有什么打算?”
李美人似有些难堪,踅过身道:“我记得曾和你提起过秉笔太监闫荪琅,你还记不记得?眼下皇上病势汹汹,有门道的早就活动开了。咱们在后宫无依无傍,还有什么逃命的方儿?等到诏书下来,一切就都晚了。”
音楼骇然:“你要去和那个太监谈条件吗?这会儿去,正中了他下怀。”
李美人凄恻一笑,“我在宫里孑然一身,还有什么?无非要我做他的对食,我也认了。比起死来,孰轻孰重,压根儿用不着掂量。”
她目光死寂,想是已经打定了主意。音楼起初还浑浑噩噩,到现在才切实感受到末日的恐慌。真的走投无路时,没有什么舍不下。所谓的对食,就是太监宫女搭伙过日子。虽然没有实质内容,但对外形同夫妻,跟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内廷女子能选择的路不多,一些有权有势的太监膨胀到了一定程度,最底层的宫女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畸形的自尊,于是就把触手伸向了有封号的低等宫妃。皇帝呢,则因为太过依赖那些宦官,加之女人众多顾不过来,即便是有耳闻,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
配给太监,但凡有些傲骨的谁愿意?真要相安无事倒罢了,岂不知越是高官厚爵的,反倒比外头寻常男人更厉害。早年曾经发生过执事太监虐杀对食的事,皇帝听说后不过赏了二十板子,轻描淡写就把案子结了。李美人要是自投罗网,岂不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她想劝她三思,可是又凭什么?生死存亡的当口,各人有各人的选择。李美人迈出去,穿堂里回旋的风卷起她的衣角,愈行愈远,隔着蒙蒙雨雾瞧不真了。音楼攀着棂花槅扇门呆呆目送,心里觉得惆怅,都去找出路了,只有自己,人面不广,除了等死没别的办法。
“主子,咱们怎么办?”她在地心转圈的时候,婢女彤云亦步亦趋跟着,“您说李美人要是说服了闫太监,会不会拉咱们一把?”
音楼抬眼看房顶,“这时候,谁顾得了谁?”
彤云带着哭腔跺脚,“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您快想辙呀!”
她也不想坐以待毙,可是有劲没处使,怎么办呢?
“你是让我找太监自荐枕席?我好像干不出来。”她讪讪调开视线,“再说就算我愿意,也没人要我啊!司礼监今儿肯定吃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要不上御马监试试?御马监现在也是香饽饽……你说沦落到叫太监挑拣,心都凉了。”
彤云感到一阵无力,“活着要紧还是脸面要紧?其实别处瞎忙都没用,眼吧前只有司礼监的掌印、秉笔握着生杀大权。如果能攀上掌印太监,那咱们的脑袋就能保住了。”
掌印太监提督东缉事厂,是太监里的头把交椅,权倾天下。音楼才进宫的时候,曾远远见过东厂的人。头戴乌纱描金帽,身着葵花团领衫,领头的系鸾带,穿曳撒,左右绣金蟒,从汉白玉的月台上走过,那份气势如山的排场,叫她至今都不能忘。
可是太监阴狠狡诈,哪里那么容易攀交情!她靠着朱漆百宝柜嗟叹,掌印太监肖铎媚于侍主,凭借着帝后宠信设昭狱、陷害忠良。同他打交道,只怕死得更快啊!
第2章 春欲暮
天色渐暗,雨势似乎小了些。昼夜交替的时辰,外面的暮色是稀薄的蓝,恍恍惚惚,有些分不清是黎明还是傍晚。
“干爹喝茶。”曹春盎虾着腰呈上个菊瓣翡翠茶盅,觑见他脸色不好,小心翼翼道,“干爹连日操劳,儿子给您按按?”
有头有脸的太监时兴收干儿子,儿子尽心尽力孝顺干爸爸,当干爹的也疼儿子,父慈子孝真像那么回事。肖铎也有个干儿子,去年九月里才认的,十二三岁,很伶俐的一个孩子。照着外头成家立室的年纪算,爷俩相差十来岁,断乎养不出这么大的儿子来。在大内不一样,就像贵人们养猫儿、养叭儿狗,有人干爹叫得震心,图个热闹好看。
他没应他,曹春盎很乖巧地转到他身后。皇帝左右专事按摩的人,服侍起来很有一套。拳头虚虚拢着,肩头后脖子轮一遍,五花拳打得又脆又轻快。
他闭目养神的当口,秉笔太监闫荪琅托着六部誊本来,低声道:“内阁的票拟都已经送上来了,皇上眼下病重,依督主看,这批红的事儿……”
“搁着。”他捏了捏太阳穴,“我先头那番话不过是为稳定军心,那帮顾命大臣不动刀剑,舌头能压死人。皇上要是能开口,批了也就批了。这会儿连话都说不出来,谁敢动那一笔,闹得不好就是个话把儿。外面市井里有传闻,管我叫‘立皇帝’。这话从何处来,已经打发东厂的人在查了。这么大顶帽子扣下来,万一秋后算账,几条命都不够消磨的。”
他这份小心,倒叫几个秉笔、随堂心头一震。大伙儿交换了眼色,趋身道:“督主这么说,真令属下等惶恐。莫非有什么变数么?”
提督东厂的掌印,向来只有算计别人的份。朝中不论大小官员,提起东厂哪个不是吓得魂飞魄散?督主突然这样谨小慎微,叫底下人觉得纳罕。
肖铎知道,这帮人作威作福惯了,冷不丁给他们抻抻筋就瞧不准方向。他手里捏着蜜蜡佛珠慢慢数,边数边道:“多事之秋,还是警醒点的好。皇上这病症……往后的事儿,谁也说不清。”
江山要换人来坐了,话不好说出口,彼此都心照不宣。闫荪琅呵腰道是,捧着奏本退到了一边。
“工部的奏拟,不知督主瞧过没有?”底下随堂太监道,“上年黄河改道,于临漳西决口,东南冲入漯川故道。当时工部奉旨治水,才半年光景,所报的开支已经大大超出预算……”
话还没说完,被肖铎抬手制止了。他起身踱到门前,挑了帘子往外看,雨丝淅淅沥沥飞进檐下,灯笼上的牛皮纸受了潮,朦胧间透出里面飘摇的烛火。天真冷啊,竟同隆冬一样呵气成云。他搓了搓手背,拉着长音道:“再不出太阳,治水的亏空只怕更大了。横竖不是咱们的事儿,该操心的是内阁首辅。说到底咱们是内监,皇上龙体抱恙,头等大事还是圣躬么!传令其他十一监,这两天值房别断人,不定什么时候就有旨意的。我头疼,旁的不多说了,还要回东厂一趟。”又哦了声,“荪琅跟着,我有话交代。”
他披上流云披风迈出门,这回没带人,只有曹春盎在边上打油伞随侍。闫荪琅趋步跟上,只听他说:“把乾西五所的名册归归拢,殉葬的人当天就要上路,别到时候手忙脚乱摸不着头绪。”
闫荪琅应个是,“督主放心,这事儿今天已经在筹备了。先帝从葬六十八人,这一辈儿不能越过次序去。暂时拟定六十人,届时花名册子呈您过目,该添的或是删减的,听您的示下。”
他嗯了声,抬手扣披风上的鎏金压领,漠然道:“以往随葬都有定规,什么品阶几个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事要办得漂亮,恰到好处才不至于翻船。我前儿还想着歇一歇来着,眼下看来是不能够了。批红这头短了,厂卫那头更要兼顾起来。这当口还不比平时,蠢蠢欲动的人多,撒出去的番子探回来一车消息,不拿几个做筏子,东厂在他们眼里成了吃干饭的衙门。”
东厂直接受命于皇帝,四处潜伏,监视各地官员一举一动。比方有一回詹事府几位同知和赞善大夫赌钱,前一晚台面上多少输赢,第二天皇帝笑谈间就透露出来了,吓得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大难迎头袭来倒还罢了,这份时刻遭到窥伺的恐慌才直慑人心。皇帝病危,东厂的活儿却不能停,越到这种时候越是风声鹤唳。闫荪琅是他的心腹,知道他办事一向狠辣,否则年轻轻的不能坐上这把交椅。既然执掌东厂,干了就是一辈子。这种职权不容你卸肩,结了那么多仇家,哪天下台就意味着活到头了。
至于他说的办得漂亮,自然是指后宫的动向。皇帝晏驾,一大帮女人要跟着倒霉,脑子活络的都不会坐以待毙,走后门托人,不管是钱财收受还是人情交易,不说完全秉公办事,至少面上交代得过去。这头干净了,才好留下名额填塞那些原本不该死的人。两边匀一匀,遮盖过去了,差事就办下来了。
闫荪琅诺诺称是,“圣上只有荣王一子,督主是要勤王?”
他一手挑着灯笼缓缓前行,听他这么说微侧过头瞥他一眼。昏暗的火光照亮他的半边脸,似阳春白雪又冷冽入骨。油靴踩过水洼,朱红的曳撒下摆撩起一连串弧度,膝澜上金线绣制的蟒首面目狰狞,他却馨馨然一笑,“勤王?这主意倒不错,兴许还能借机洗刷我的恶名。只可惜我名声太坏,这辈子是当不成好人了。”
他模棱两可的话叫闫荪琅一头雾水,即便是最信任的人,他也从不把心里的想法同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知道太多,只要按他的吩咐行事就行了。
“东厂的人进不了宫,万岁龙驭上宾之时还得司礼监出力。丧钟一响即刻派人把守住承乾宫各门,不许任何人出入,到时我自有道理。”行至延和门前他顿住了脚,接过曹春盎手上油伞让他们回去,自己独个儿往贞顺门上去了。
贞顺门内是太监把守,过了横街,对面由锦衣卫驻防。肖铎地位显赫,内官们远远看见他来了忙落钥。闫荪琅目送那身影逶迤出了琉璃门,扭头看曹春盎,“你听出什么来了?”
曹春盎吸了吸鼻子,仰脸笑道:“督主的意思让您别光顾着捞银子找对食,好歹莫留什么把柄叫人拿捏住。”
闫荪琅照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小兔崽子,爷们儿是说这个么?”
爷们儿?缺了嘴子的茶壶自称爷们儿,不嫌磕碜么?曹春盎皮笑肉不笑地应承:“是是是,我说差了。”他拢着两手往他伞下挤了挤,“督主吩咐事儿,咱们照着做,准错不了。那什么……他老人家最近总闹头疼,置了府第也不常回去。依我说,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了位干娘。咱们太监虽净了茬,心里还拿自己当男人看。有个知冷热的人照应着,没准儿头疼的毛病就好了。我听说女人身上的香气包治百病……嘻嘻,闫少监应当是最知道的。您别光顾自己,也给督主看着点儿呀!”
闫荪琅白了他一眼,半大小子懂个屁!再得意的人儿,想起自己的残疾也难受。要女人容易,可得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天天戳在眼里,时刻提醒自己下边缺了一块,换了没脸没皮的人也就算了,像那位这么敏感精细,不定心里怎么想。给他塞女人,谁触那霉头!
第4章 红粉面
第二天天放亮,辰时三刻云翳渐散,缠绵了一个多月的阴雨突然结束了。
天地洗刷一新,空气里有新泥的芬芳。似乎是个好征兆,一切的不顺利都该烟消云散了。抬头看穹隆,高高的、宽广的,音楼还在惊讶天这么蓝,六宫的丧钟就响了。
几乎同时,十几个换了丧服的太监手托诏书进了乾西五所。风吹动他们襆头下低垂的孝带,死板的马脸像阎罗殿里讨命的无常。打头那个往院子里一站,扯着公鸭嗓喊话:“人都出来,有旨意。”
这旨意是什么,不言自明。担心有人和稀泥,下巴一抬,身后的内侍分散出去,把屋里的人统统赶了出来。
低等宫妃不像那些品阶高的,有独立的寝宫。她们通常几个人共用一间屋子,东西五进的院落各处住满了人,从头所到五所,凑起来足有四五十。
音楼随众人到殿外候旨,推推搡搡间匍匐在地,听台阶上司礼监太监宣读手谕,内容很简单,也不需要过多交代——“大行皇帝龙御归天,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就完了。
这样的命运虽然早预料到了,真要赴死,又觉得像是坠进了噩梦,怎么都醒不过来了。
四周围哭声震天,音楼跪着,腿里酸软无力,伏在地上起不了身。前两天还心存侥幸,总以为皇帝尚年轻,至少还有几年活头。谁知道这才多久,居然真的晏驾了。
她脑子里茫茫一片迷雾,什么想头都没有,光知道自己刚满十六,离家进京应选,空得个才人的名号,还没咂出做娘娘的味道,就要随那未曾谋面的皇帝一道去死。
她是迟迟的人,快乐来的时候感觉不到大快乐,悲伤突袭也不知道哭。耳边呼啸的是尖利的喉咙,她只感到害怕,害怕得浑身发抖,手脚都僵了,寒意从四肢百骸渗透攀爬,笔直插/进心坎里。
“哭什么?这是喜事儿,是祖上积德才有的造化。随侍先皇,朝廷自有优待。往后家里人受了爵,念着娘娘们的好,也不枉一场养育之恩。”司礼太监不伦不类的开解不能平息人群里的惊恐惶骇,谁都没拿他的话当回事,他也不甚在意,对插着袖子吩咐,“来呀,伺候娘娘们换衣裳。误了吉时。谁也担待不起。”
簇新的白布散发出一种濒死的臭味,腰子门外涌进来一帮尚宫局的人,抖着衣领展开了早就备好的孝服。大半的人被敕令吓走了魂,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换衣服了。那些尚宫粗手大脚上来摆弄她们,扒了身上花红柳绿的褙子,摘了头上锦绣堆叠的钗环,右衽交叉,腰上带子狠狠一收,一个就料理妥当了。
音楼被推得团团转,勉强站住了脚四下环顾,所有人都不甘,每张脸上都是痛苦和绝望,却没有一个奋起反抗的。这可悲的年代,挣扎也是徒劳,该死还得死。慷慨上路家里能得荫蔽,要是不那么情愿,最后白白牺牲,什么好处都叫你捞不着。
所以得笑着去死?她打了个寒颤,本来还盼着家里哥哥侄儿进京能来探探她,现在倒好,只要逢年过节祭拜祭拜就成。隔山望海也不打紧,她一抬脚就过去了。可是殉葬者的魂魄会被镇压住吧?也许封在墓穴里,永不得见天日。
不知道李美人怎么样了,她没在听旨的人堆里。因为不住一个屋,她去找闫太监后就没露过面,音楼也没再见过她。也许他们相谈甚欢,李美人已经搬出乾西五所,住到闫太监的处所去了。强权之下不得不低头,给太监做对食听起来很悲情,但总算保住一条命,音楼也替她庆幸。
死要做个饱死鬼,就像上刑场前有顿断头饭一样,这是人世间最后的一点施舍。宫门大开着,尚膳监进来一溜太监,两两搬着一张小炕桌,殿外的空地上铺好了毯子,把那些炕桌整整齐齐摆好,请她们入宴辞阳。这种时候谁能吃得下饭?音楼回头看,彤云还在她身边,宫女不用去死,还可以扶她上春凳,伺候她把脑袋放进绳圈里。
她看着她,嘴唇翕动,说不出一句话来。
彤云哭得撕心,“主子……主子……”
她到这会儿才觉得鼻子发酸,临终遗言带不出去,对爹娘再多的牵挂也不过是空谈。还好家里有六个兄弟姊妹,死一个她,痛了一阵也就过去了。
“箱笼里有四五两银子和几样首饰,我用不上了,都给你。”她想想,还是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我这算不算死于非命?将来还能不能投胎转世?”
彤云安慰她,“您这是殉节,阎王爷见了您也会客客气气的。”言罢又淌眼抹泪,“我叫您想辙的,您不听,落得眼下这田地倒好么?”
她也不想死,被逼着上吊不是好玩的。要想跟李美人一样,得有路子,至少人家相看得上你才行。她这人生来桃花运弱,君恩轮不着她,连太监都没一个对她示好的,想想实在失败。
事已至此,没什么可说的。她坐下来喝了口汤,还没咽下去,司礼太监高唱:“是时候了,娘娘们搁筷子移驾吧!”
音楼听见嗵嗵的心跳,一声声震耳欲聋。彤云来搀她,她腿里没力气,半倚在她身上,歪歪斜斜跟着队伍往中正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