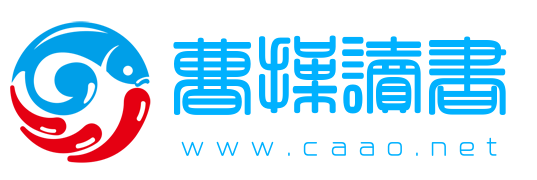长枪当旗笔趣阁版
书籍简介

寒燚是什么?这是一个自醒来便一直围绕在珏心头的问题。为了得到答案,失去记忆的珏开始了自己的旅途。但这一路上并不安稳,众多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几欲掀起腥风血雨。计谋诡道,残酷厮杀,都将一一上演。
内容简介
寒燚是什么?这是一个自醒来便一直围绕在珏心头的问题。为了得到答案,失去记忆的珏开始了自己的旅途。但这一路上并不安稳,众多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几欲掀起腥风血雨。计谋诡道,残酷厮杀,都将一一上演。
内容在线试读
永星界陆东南有一座高约六百丈的孤山,名曰凌物。凌物山顶有一处花开烂漫永不凋谢的梅花林,无甚名号。只是在这幽香园林深处,有一颗高大的梅花树,枝头有梅花,树下有木屋。
阳光正好,树影斑驳,木屋外的梅花树下,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边。
中年男子身周有晦涩能量流转,阻挡了投来的视线,让人看不清容貌,只能勉强看出,他外罩一件墨色深衣,乌黑长发用了一根树枝束起。
这位中年男子是寒燚太上。
太上气质儒雅温和,跪坐桌前,青色木桌上翻开着一本泛有白色光晕的书籍。
书页材质看不出来,透过光晕,隐约能看见上面从右到左竖着写有一段话:
“薄暮时分,轮回炉中,我从漫漫长夜醒来。
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归途,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
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回到了白沙。”
太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如雕塑般安静注视着这段话。
忽然有风来,吹入树枝间,沙沙作响,花香轻浮。
太上眼眸微动,微微抬起脸,仰望枝头摇曳的梅花。
“已经……这么久了吗?”
太上的声音轻轻响起,透着大梦初醒般的恍然。
而后太上缓缓低头,看着书上文字。
“又失败了啊。”
轻叹一声,太上抬起修长白皙的手指,轻轻点在书页上。
乍如日出雪融,书本表面的白色光晕消失不见,得以清晰地看到这段文字的落款。
珏。
“这次,是最后一次了。”太上再次仰望枝头,一朵浅粉色的花骨朵在缓缓绽放。
“要开心啊,珏。”
…………
夏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正月初五,夜。
星陆东列班国解语省,花府。
月黑风高,杀人放火。
年仅七岁的花人天缩在狭小的假山洞里,轻轻啜泣。
外面是一蹿几丈高的火焰,散发内力光芒的刀剑乱舞,血光四溅,惨叫声不绝于耳。
小小的花人天害怕得不敢动弹,身体蜷缩,双手堵住耳朵,似乎这样他就可以忘记兄长被杀时发出的惨叫。
忽然有一支手用力把他从洞里扯出,提起他的衣领,似乎是在辨认样貌。
受到如此惊吓的花人天立刻惊恐大哭起来,泪眼朦胧中,他看见提着他衣领的男人右胸处有用夏文绣的“神”字。
他依稀听见男人用夏语喊:“东西找到了!”
什么找到了?花人天不明所以,放声大哭的他只想扑进温柔母亲的怀抱,不,就算现在出现的是最严厉的父亲,他也要扑进去!
提着他的男人突然发出一声惨叫,随后松手倒地,他也跟着瘫倒在地上,然后有一双有力的大手抱起了他。
“杀。”抱着花人天的男人迅速下令,冷酷果断。听音调是一位年轻男子。
“别怕,别怕,”似乎是感受到怀里男孩的恐惧,年轻男子轻拍着他的背,低声说,“你要活着。”
“活……着。”哭累了的花人天喃喃低语,通红的眼睛慢慢阖上。
…………
夏历一千九百七十八年,四月初三,夜。
夏陆天夏国煌州,州治煌州城。
“走水啦!走水啦!”
“走水啦!快救火啊!快救火啊!”
“哪里走水了?哪里走水了啊!”
“北丈书院!城北的北丈书院!那里走水了!”
“阿、阿翁……呜呜、呜呜、呜呜……阿母,我……我好、好怕啊呜呜呜呜……”
“大家快跑啊!快出城啊!全城都要烧起来了啊!”
“快跑啊!快跑啊!”
天空被火焰烧红的夜晚,人们或慌张或悲伤或恐惧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煌州城。燃烧着大火的北丈书院外,卫律与百姓焦急地提着水一桶一桶地冲向火区,可是火势太猛,人们拼命也只能暂时阻止火区的扩大,而无法彻底扑灭大火。
在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北丈书院里,有两队人马正在怒吼交战,金铁交鸣,灵气杂乱。
“刘鸣沙在这儿!”
不时有嘶吼声在不同的地方响起,瞬间便引来两方人马的拼死搏杀。
噼里啪啦的木料燃烧中,兵器相接和负伤痛哼的声音尤其突出。
而那个叫刘鸣沙的男人,现在正和一位自称名为影政的年轻人藏在书院最边缘的一间木瓦房里。
刘鸣沙今年三十七岁,天夏国人,相貌平平,独居,是北丈书院一位并不起眼的先生。这次厮杀正是围绕着对他的争夺展开的。
此时,满头大汗的刘鸣沙穿着儒袍,蜷缩在房间一角,脚边有一根短小的蜡烛在微弱地发光。读书人未曾习武的孱弱身子刚经历了一场极限奔逃,正在微微颤抖。
身着黑衣的影政单膝跪在门后,用粗布轻轻擦拭短剑上的血迹,同时上身虚靠在门框处,仔细感受外面的动静。
这里距书院稍远,不时有人跑过,短时间内,还算安全。
但影政很着急。事发突然,当他们在北丈书院见到刘鸣沙的那一刻,敌人便点起了火,自四面八方杀来。他们仓促应战,无奈敌众我寡,尽管年轻气盛的他心中满是不甘,但为了保住刘鸣沙,他只得在一刻时前靠着同伴的拼死掩护带着刘鸣沙撤了出来。
短剑擦净归鞘,影政看向刘鸣沙,看向这个他已经观察了半年之久的普通中年男人。
其实也不能说普通,毕竟是能引起他们拼死争夺的对象,说刘鸣沙普通,是对豁出性命来争夺的他们的侮辱。
那刘鸣沙不普通在哪呢?
影政微微眯了眼,以往听过的传闻在脑海里回响。
刘鸣沙忽然看向影政,目光平静。
突兀的举动立刻引起影政的注意,他下意识看向刘鸣沙,两人一时对视。
刘鸣沙对着影政微微一笑。
那副笑容就像有魔力,让烦躁的影政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然后种子发芽,这个想法在脑海里迅速膨胀,挤走理智,挥之不去。
试一试?
影政眯起眼,轻轻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
微微刺痛。
那就试一试。
……
夏历一千九百九十八年,腊月初五,正午。
麦鸣岛亚玛特兰,朝府总部。
一望无际的大海,蓝得深沉,白云兜兜转转的蓝天下,淡褐色的海鸥成群划过,留下漫天的“喔喔”声。温暖的阳光落在海浪怀里,映起一片金光闪闪的波澜,偶尔有鱼跃出海面,更添勃勃生机。
“麦鸣岛的冬天就是这么美。永不结冰的永星海上,成群的凝线鱼从南方的喀欺尔特海出发,一往无前地向东列班群岛游去,途中它们要穿过特码琅岐大漩涡,在那里丢下无数同伴的尸体,只为了种群的延续。”身着西鲁因恩式服饰的中年金发男子仰头灌下瓶子里最后一口酒,深蓝色眸子深情注视着大海,“格拉列兰岛的大转角是观赏凝线鱼迁徙的好地方,不知尊者大人看了没,那样的悍不畏死,真是太壮观了。”
他靠在墙面大小的兰窗上,回头看向坐在桌前精神矍铄的老人,晃了晃空荡荡的酒瓶。
老人身体健朗,穿着绣有圆形图案的紫色袍服,外罩淡赤色的棉袍,有一头天生银白色的头发,丹凤眼不怒自威,浅蓝色眸子里流淌着历经岁月的平静。
揉了揉眉毛,老人一只手端起酒杯,轻轻晃动,另一只手翻动公文,目光不曾转移:“大转角太远,在这里看看就好。周像,我得提醒一句,你的假期已经提前结束了。”
周像低笑,放下空酒瓶走向酒柜,用抱怨的语气道:“尊者大人可真是啊,居然会提前结束您忠诚朋友的假期。唉,真是伤心。”一边说着,他一边取出一瓶新酒,敲了敲瓶身,然后侧耳倾听酒液与瓶壁碰撞的美妙声音,语气陶醉,“我得再喝一点尊者大人的藏酒,才能开心努力工作。”
“大可不必。”老人摇摇头,放下酒杯,和上公文,靠向挑花软垫椅背。
“你已经喝光了我一瓶夫人笑了,再说,假期后面会补给你,”老人揉了揉眉毛,指着周像手里的酒,无奈道,“还是聊聊今天的正事吧。”
星历元年正月初四,夏陆天夏署州桂鱼郡开必县,开必县城。
在二十三年前,开必县还不叫开必县。设县于夏朝的她有一个传承上千年的名字——丰安,后来挑灯查遍了史书古籍几乎看瞎了眼睛的天夏国史官们才从字缝里看出,这名字取的是“丰富安民”之意。
若是在二十三年前说这话,县里的人们大抵会阴地里狠狠地朝这些史官老爷们啐口水。因为龙井泉不再涌泉的丰安县,就只是天夏西南部署州的一个一人口不过千户的小县,无甚特产,庄稼丰年也仅供自给,灾年就更别说了,一家人整整齐齐出县乞讨。
直到二十三年前,丰安县城南郊桂山脚下沉寂已久的龙井泉重新涌出泉水,这一切才得到了改变。
龙井泉重新喷涌,一夜积水成池,池上云雾缭绕,神异非常;池中红鱼偶跃,常高于桂花枝者,便是古鱼乘桂。
乘桂,不知来由,古籍只道此泉独有,乃当年丰安县繁盛之根本。此鱼通体红得鲜艳,大小不过成人一掌之合,味道异常鲜美,有开智明目之奇效,为夏之一绝。夏朝灭亡后,龙井泉便不再涌泉,池水也都干涸,乘桂亦是不出。此后天下大乱,列国纷争不断,此间事渐渐无人知晓,只在史书中还留有一两点墨迹。
今过七百余年,龙井泉再度涌泉。于是王公贵族的使者便接踵而至,只为一尝古人贪嘴之物。
因为乘桂跃泉次数极少,难以获得,以至达到了千金难求的地步。于是丰安改名开必,取“井门壹开必乘桂”之意。
龙井村就坐落龙井池旁。原本不过数十户的小村庄,在龙井泉重新喷涌后,便有不计其数闻风而来追逐暴利的“渔夫”涌入龙泉村,至今人口已有数百户之多。
龙井村北靠桂山,整体地势自北向南倾斜,而龙井池就坐落在村子的最南边,村口刚好在龙井池附近。
龙井池约三百步之围,以石垒边,略呈圆形,池中央,有奇石高出池面,石上有口,碗口大小,池水与乘桂皆从此口出,这便是龙井泉。
正逢年节,池边的人少了许多,但仍有百十来位汉子扎在一堆,就着清水薄饼谈天说地,谈话声和哄笑声此起彼伏,只是看着热闹和谐充满欢快气氛,但一个个视线却都是离不开泉眼。
村口不远处,一袭深衣的花人天跟在身着麻衣的瘦高男子身后,向龙井村一步步走去。
将入龙井村,瘦高男子停步侧头,声音透着模糊感:“还有些时间,若有未竟之事,就这时去做吧。”
花人天施礼:“谢大长老。”
大长老点头,转身向前。
花人天目送大长老在围着龙井泉的汉子们好奇的目光中进入村子后,转身往开必城走去。
他要去吃珠饺。
珠饺,将珠冠蛇剥皮剁碎后用特制面皮包裹,放入滚烫酱汤中焖煮,待酱汤煮干,再将珠饺放置冰中四分之一刻,因珠冠蛇特性,取出珠饺时,定是皮白馅粉、外冷内热。一口咬下,瞬间的凉爽后,是恰到好处的温暖,给人冬天冒雪回到暖和房屋的满足感,实乃冬春之季不可或缺的美食。
正是年节走人户时分,人迹稀少的开必城西市内,花人天在一家不大的食店里端着一碗珠饺,细细品味。
“年节日子里,难得你还开着。”花人天箕坐着背靠凭几,口中呼出热气,然后拿起一边的小棍撑起窗板,看向外面冷清的街道。
“知道你好这一口。”身材矮小的店小二站在一旁,轻笑回忆,“记得第一次见你,也是年节。你当时几岁大小,见着我们这些生人也不害怕,扯着张堂座袖子就说‘要吃珠饺’。”
花人天收回视线,看向面带笑容的店小二,也笑了:“你们当时衣服上全是血,踹开门把肆厨拎起来的时候差点没把他吓哭。”
店小二笑着笑着,逐渐沉默。
花人天低下头,慢慢拨弄盘里的珠饺,似乎是在回忆很多年前的那一碗。但是年代太过久远,香气都已模糊,实在是回忆不到,于是他摇摇头,不再回想,挑起一只珠饺就塞进嘴里,微微张口吐出热气。
接连吃了几个后,他抬起头来,望向店小二:“会里知道我到开必县了吗?”
“你六天前来的时候,我就送了信,估计已经从岐巍派人来了。”店小二一边低头用抹布擦手,一边回答。
“你不回圣会了?”花人天放下碗,端起杯子喝水。
“走不了啦,”店小二放下抹布,坐在花人天对面,捶捶腿,“家里的女人恋旧,死活不愿意走,我便也不走了。”
花人天挑起珠饺的手微微一顿,接着问道:“我记得你有孩子。”
店小二咧咧嘴:“前年去看龙井池的乘桂,掉池里啦,就埋在桂山脚,也近。”
沉默。
“我不是叛逃。”花人天忽然说。
“什么意思?”店小二转头看向花人天。
只见花人天一股脑地把剩下的珠饺都送进嘴,费了很大劲吞下后,他看向店小二,语气略急:“只有离开圣会,才有一线生机。”
不明所以的店小二苦笑挠头:“我只是
花人天站起来,没有再说话。
“但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这一切对你并不公平,”店小二声音很轻,“尽量跑远一些吧,花人天。”
身子晃了晃,花人天微微点头,窗外黑夜逐渐笼罩天空,他最终再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几刻时后,当花人天来到龙井村时,太阳已将大半个身子都藏在月亮后面了,大长老正端坐在龙井池边,安静烤着乘桂,原本热热闹闹的龙井村格外寂静。
花人天平复呼吸,恭敬行礼:“大长老。”
大长老没看花人天,随手将烤焦的乘桂丢进池子,起身径直走向桂山。
花人天恭敬跟在大长老身后。
到了桂山山脚,大长老停下,递给花人天一枚白玉,淡淡道:“滴血。”
花人天神色不变,从袖中抽出小刀划开指腹,红色血液一点一点滴在玉上。
白玉仿佛有灵性般迅速吸收了花人天的血液,开始发散出白色的光晕。
待光晕凝实,大长老才面无表情地收回白玉,开始登山。
与此同时,在距开必县近三十里的官道旁,有人举着火把。
已是不惑之年的张正策马来到,他身穿沾满灰尘的黑衣,神色有些疲惫。
待看清举着火把的白衣年轻男子模样,他才勒住缰绳下马,行礼道:“郇首座。”
“张堂座晚好,这位是影政影堂座,这位是扬朗尔格·克莱顿堂座,”白衣年轻男子——郇羞没有废话,他点点头,侧身让张正看到他身后的两个人。
一位是四十几岁的高瘦男子,身穿黑色劲装,仿佛浑身都融入了黑夜之中,连气息都难以察觉,另一位是三十岁左右的英俊男子,身着淡蓝色云纹袍,丰神俊朗。见张正看来,两人都对他颔首致意。
“我记得你们认识。”郇羞看了看三人。
高瘦男子是影政,英俊男子是克莱顿。
“是老朋友了。”借着光亮,张正对他们点了点头。
“那好,事态紧急,你们尽快出发吧。”郇羞对三人行礼告别,随后急匆匆离开了。
“你不是一直在负责花人天吗?”影政靠近张正,疑惑问道,“怎么还让他跑到天夏来了?”
“长老会的大长老帮他逃走了,一直从星陆跑到了夏陆。”比影政大四岁的张正声音疲惫,“三天前接到线报,他在开必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