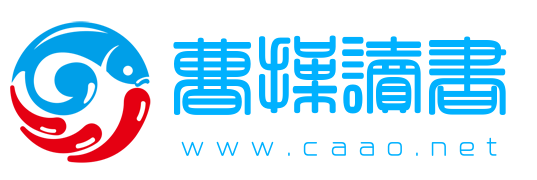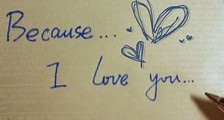【从疫情谈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篇——公共信息中的谣言与言论自由!
来源公众号:凯申日记本
微信ID:changtalk
第一篇:法律层面如何面对下一个“新冠”
年初武汉政府的“处理8名造谣者”的操作,在疫情扩大化后,被反复拿出来指责。有网友认为,如果当初没有处理这些所谓的“造谣者”,而让这些信息散播出来,大家就有警惕了,疫情不会像后来的历史那样进入爆发期。有些网友还进一步引入了“吹哨人”这个词。(注:为便于理解,本文也会使用“吹哨”这个词,但不完全是西方社会中的含义)
八名“造谣者”的身份,现在还不是完全明确。甚至李文亮医生本人究竟是不是在这八人名单之中也不好说。李医生的训诫书是在1月3日签的,但,@平安武汉 关于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的消息,则是在1月1日就已经发布了。换句话说,当初因发表疫情相关消息被处理的,也有可能比八人更多。
前几天有个消息,说有个确诊病例20多天体温没有异常。这个消息,放到一个星期前,还是很惊悚的。放到两个星期前,可能会引发恐慌。
但是几天过去了,社会上反应比较平淡,也没有因为这个扩大隔离期的时长或者更加恐慌。毕竟大家都麻木的差不多了。什么气溶胶传染,什么粪口传染,都听说了一遍。恐慌达到一个阈值之后,就没法再轻易提升了。日子还是要继续过。
这其实也给政府提了一个醒,在一定程度内,没有必要太害怕“恐慌”。
过去我们网络管的相对比较严,人们听到的恐慌性的消息比较有限,受的刺激不多,阈值较低;结果是听到一个什么事,不管真的假的,可能就在有些地方小规模恐慌了。
但如果政府对“恐慌信息”保持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容忍阈值,让人们经常受到各种刺激,经受锻炼,比如三天两头就“恐慌”一次,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变得麻木了。因为恐慌的消息可能多,但社会本身基本盘在物理上并未发生大的变动,还是稳定的。这样大部分恐慌的消息经常自己就会被证明不实,比如某人听信谣言抢了一个月的盐,接下来却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就长了记性,以后再听到恐慌消息,就要自己掂量掂量了。
政府现在把网络管的严,相当于把大部分恐慌消息都暗暗消灭于无形了,群众接受不到锻炼,信息刺激很少。“恐慌灵敏度”就会比较高,稍微有流露出来的被听到,就会紧张。这时候反而对恐慌没有抵抗力。
在恐慌中时时刻刻经受锻炼,一惊一乍习惯了,群众对恐慌的抵抗力就会提升,或者说麻木了,这个时候反而不会恐慌了。政府如果不希望大家恐慌,其实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我们接下来做一下思想体操,设想这样的场景:
网友发布与公共卫生有关的消息?管它呢,不去理睬它,谁都能发,政府也不要去管发布者,也不要删帖,只负责发布辟谣。
这样,群众看到政府辟谣,又看到流传的公共卫生信息,可以自己去判断。如果相信谣言也没什么大事,这种信息里面谣言肯定很多,平时都被消灭了,这个时候都放出来。有人看了吓的一周没出门,但是发现其实没事,他就知道自己被骗了,下次就会选择相信政府的辟谣。
那万一有人看了之后选择相信谣言,吓的一周没出门结果不幸被炒鱿鱼了呢?这就当“自然选择”了,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和政府也没关系,他被炒鱿鱼,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要恨第一只能去恨谣言发布者,第二恨自己相信了,怎么也恨不到政府头上,因为政府辟谣了,流程上完成了,不用负责。这样政府就没有责任,也没有压力,也不用删帖了,这样同时也就保证了公民的知情权。当然,一旦放开,谣言肯定很多,辟谣不一定能辟过来,这个时候可以选影响力大的辟,剩下的那些没办法,就当给群众提供自我锻炼的机会了。但也不用删帖。初期网络上肯定会乱一乱,一年之后被骗多了就会麻木了,就不恐慌了。
越怕恐慌,不让群众经受信息冲击和锻炼,群众抵抗能力越低,恶性循环,同时政府还要背404的锅挨骂,这样的结果是双输。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恐慌,那么恐慌几次之后自然就有抵抗力了。
2019年12月30日晚,有人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张图片,说是有SARS出现了。
他告诉周围的人,说有点恐慌,是不是应该赶快去屯一些口罩?
甲说:这种信息我上个月看到过三次了,结果屁事没有。
乙说:我国庆节还看见一个说华南海鲜市场有埃博拉的,吓的我两个月都没买野味吃,亏大了。
丙说:这种网上谁都能说的话你也信?我现在就给你上网发一个你信不?
丁说:这半年我SARS、艾滋、埃博拉、H7N9、鼠疫、霍乱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平均见过两次了,淡定淡定。
众:继续出牌啊,啥事没有,别吓自己。
你看,这样还用“训诫”吗?根本不用,社会上也不会出现恐慌。大家听“狼来了”听多了,就根本不去理睬了。
强令群众不相信,这维稳水平太低了,让群众麻木之后主动不去相信,自己还片叶不沾身,这才是真正高效的维稳。
但是这样效果好吗?政府倒是甩了锅,但真的疫情来了,被信息轰炸疲惫的社会同样也会是没什么反应。
有的网友提到“吹哨人”,首先脑子里的场景可能是这样的:在一片万籁俱寂的暗夜,突然空中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声。过了一会,一间屋子亮起了灯,接着,更多窗口变得明亮了起来,人们拿着猎枪,三三两两地警惕走了出来……
但实际上,如果任凭各种真假不分的信息平时就不受阻拦地传播,就相当于空气中时时刻刻充斥着真假不明的哨子,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声音污染,而社会的神经系统接收到“过饱和”的信息冲击后,就觉得不过如此,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后就算真的有“真哨”响起,反应也就平平了。
武汉政府在疫情初期的迟钝确实非常糟糕,但最错误的地方,还不在于它淡化了疫情的信息公开(当然,这事本身的定性肯定是错的)。
有网友幻想,如果武汉从1月1日起就说可能人传人,那么大家就都警惕了,戴上口罩了,病毒也就不会传播开了。
然而,现在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病毒也传播到了日本、中国香港、东南亚等地。有些地方的疫情,已经相当于12月底的武汉了,此时可不再需要新冠的“吹哨人”了吧,而且有现成的“作业”可以抄。但是现在仍然是动作迟缓,大批人员在公共场合密集聚集,店里人头攒动,政府也没有开展什么有力的社会管制,很多人都不当回事,连口罩也不戴。
所以说,就算排除了“假哨”的干扰,就算告诉社会这是“真哨”,单靠原子化社会的各个公民通过网络上了解的信息,去自觉警惕,是无法有效防疫的。
一张微信群里的图片,就算再传播,能被总人群中的多少人看到?这个比例恐怕不高。而看到的人众,能有防疫意识,去主动戴口罩的,又是一个不大的比例,特别是年龄大的人。别的不说,当全国进入防疫状态后,政府三令五申之下,还有很多中老年人不愿意戴口罩、并出门走亲访友呢。你就可以设想,当整个社会处于自由原子化状态下,几张微信群里的图片能起到多微弱的作用了。
而要成功拦截病毒传播,需要社会中很高比例的人都去做防护。但如果仅仅是“吹哨信息”不被“训诫”掉,那么当疫情进一步扩散后,只会让警惕的人群比例提升到“挤兑医疗资源和超市”的程度(这个所需比例并不高,全社会10%的人去挤兑某项公共资源,就承受不了会崩溃),但又达不到全民戴口罩不聚集不串门的程度(怎么也得让90%的人呆在家里才行吧)。
落在10%-90%这个区间里,这样的结果也很糟糕,疫情对整个社会还是会继续传播扩散,同时小范围的恐慌和挤兑也会出现。两个不利都占上了。既慌乱无助,还防范不了。
那么李文亮医生和其他信息发布者的行为,就没有意义了吗?也不是。
如果武汉政府当时没有切断这样的信息传播,随着一线医生那里关于不明肺炎的各种消息流传出来,会在网络上形成高度关注。这些关注者虽然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很低(靠他们本身的警惕去实现防疫效果意义不大),但是聚集的声音放在网络上就会被放大,形成舆情高峰和舆情压力。这种压力使得政府就要去回应。回应还不能瞎回应。比如后来武汉政府说“应收尽收”,但是网上很快就出现一些求助者来打脸。这种舆论压力最终使得收治工作产生了良好的负反馈效果。如果没有这样的网络压力,地方政府反应可能还会继续迟钝下去。
所以,当初如果武汉政府去被迫回应舆论,那就不得不去深入一线调研,倾听声音,评估严重性。并在来回几次打脸之后,做出严厉防疫措施的时间,可能会比后来的更为提前。
总结:
0、政府对公共信息的传播尺度,可以适当放宽,任其产生一定程度上可控的对群众的刺激。
1、“吹哨”警示作用好的前提,是一定程度上的信息管控带来的对“噪音”和“假哨”的屏蔽。
2、对于原子化的社会,如果政府不出手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在快速扩张的病毒面前,“吹哨”没有多少作用。
3、在具备强有力动员能力的社会中,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吹哨”可能会产生作用。但不是以【吹哨——信息传播——公众自觉防范】这条路径来起作用,而是会以【吹哨——信息传播——政府重视——社会动员——全民自觉+被动防范】这条路径来起作用。
有些网友在对武汉政府的错误反思的时候,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把问题归结于整个体制,幻想西方化的体制可以做的更好。其实不会,它顶多只是在“信息传播”这一站不会加以限制,但由于前期“假哨”和“噪音”的干扰,加上后期政府如果不愿或者无法进行强力社会动员,社会公众是不会去主动网格化生活和隔离的,而这些则是防疫的关键举措。相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则具备实现第二个路径的能力,当“信息传播”这一环在疫情爆发之后变得相对顺畅,整个路径上再无不通的节点,社会开始高效转动起来,从而体现出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动员能力。
可见,我们的社会体制对于防疫而言是有相对优势的,但缺点在于信息传播这一环。经常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像鼠疫这种登记在册进入传染病法的还好说,有预案去该做什么。但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脾气不清楚的“新病”,需要官员有为人民负责的勇气和魄力,却遇上缺乏责任心的官僚,他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压热度”,这样就断掉了“舆论压力”,整个路径就“堵塞”了,疫情就拖延了。
到这里,问题被更细致的定位了:在公共卫生或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信息,如何区分“真哨”和“假哨”(谣言)?信息完全不管控是不行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大的全能型政府,不可能真正的对这类信息实行“大撒把”不去理睬,然后在公众信以为真后说“关我屁事”的。这样不符合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民间认知,并不能撇清责任,民间到时候还会骂的。
但是,也不能完全赋予地方政府或部门随意指定“谣言”的权力,否则就会出现“懒政”——我不喜欢听到的消息,那就是谣言。
可能有网友注意到了,武汉政府在1月1日提及“处理了8名造谣者”的时候,居然没有说他们造了什么谣。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讽刺的效果:说武汉政府因为辟谣而让公众丧失警惕性,都是高估了他们的信息沟通能力,因为他们压根就没说谣言的内容是什么,辟谣要否定的信息是什么。如果没有后续媒体的跟进深挖爆出了“疑似SARS”的“谣言”内容,这个根本不配称之为“辟谣”的举动紧跟在更有冲击力的“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新闻的后面一起发布,甚至反而起不到“让人丧失警惕性”的作用(虽然“辟谣”的初衷是想降低新闻热度)。
那么,为什么武汉政府当时不愿意说谣言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将谣言内容公之于众的本身,就会起到“提示”作用,引发公众往SARS的恐怖那边去想。那么这种辟谣就成了传播,背离了初衷。
因此,可以进行这样的改革:地方政府或部门,凡是处理有关公共事务的谣言时,必须公布谣言的具体内容或者内容概括。这样,就逼得地方政府在和公众沟通的时候,无法再“懒政”,一句“谣言”把公众打发掉。它如果要再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的谣言,就只能去多方询问,找到明确的答案,然后公之于众,说服公众。
同时,也要规定,如果地方政府或部门,没有对事关本地区的舆情做出及时回应,导致进一步重大舆情或者社会秩序混乱的,属于违规行为,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
这样,两边一“夹”,你既不能“装聋作哑”,又不能“指鹿为马”,只能老老实实去调查研究,和公众正面打交道,去“排除假哨”,并通过交流沟通,恢复与群众的对话能力。群众不是反对辟谣,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愚弄,当真正的谣言和造谣者被打掉的时候,网络上普遍也是持正面支持态度的。群众不满的是:一个普通人因为说了一些真话,也没想传播,结果就被训诫了。他们自然会联想到自己,觉得自己可能也会是下一个。
因此,辟谣需要有根据,需要把“谣言”本身“晒”出来,有理有据驳斥后广为宣传。这样的辟谣才是有力的,否则,像武汉当初那种做法,连谣言是什么都不说,倒是省事了,辟了和没辟是一样的,起不到警示作用,还容易变成官员“捂嘴巴”的工具。
这样的改革是有现实意义的。过去政府部门不需要这样,是因为纸媒电视时代的单向性,这样的交流就算没有也问题不大。但现在政府和群众的交流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群众会用网络了,有网络社会的思维了,政府官员如果还停留在纸媒时代,幻想着“眼不见心不烦”,那是不可能的。轻则群众骂你,重则就像这次疫情,病毒可不会顺你的心意。
因此,如何让官员具备网络时代和群众打交道的能力,应该是接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这种改革应该是一种“顶层设计”,也就是中央规定地方政府要这样做,并对执行情况列入考核。以立法的形式也行,以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形式也可以。具体采用哪种,可以进一步探讨。
目标和任务有了,但地方政府新加了这些工作,之前又不熟悉,谁去干这些活呢?
一个建议,是由地方宣传部门牵头,组建各地的网络谣言辟谣中心,人员编制不增加。执行效果作为对地方宣传部门的考核指标。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把政府部门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工信部、公安部、科技部这类,日常工作KPI和机构设立初衷方向一致或者大致一致;另外一类是台办、宣传机构、统战机构这种,平时的KPI难以体现机构设立初衷,也难以考核实际效果,因此整体KPI就向与机构设立初衷无关的官僚化事务性方向倾斜,最终变成一个“为了设立而设立”的部门。
宣传部门也是这样,设立初衷应该是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有效信息沟通而设。但沟通效果无法量化,没办法考察,于是地方宣传部门就倾向于那些能够量化和考核的东西,比如在大报上发了几篇稿子,比如官微有了多少个粉丝,比如某篇宣传有多少个全国级媒体转载……但这些是与“沟通官民”的设立初衷不一定完全一致的。这也导致官僚化的宣传机构不接地气,只满足于能够量化的KPI,而干脆无视原本就无法考核的设立初衷。
网络时代,宣传机构怎么改革呢?原先对基层的报道能力还是要部分保留,不然市场化的媒体不一定会关注基层那些没有流量和吸引眼球能力的干部群众。但是那些服务于官僚机构本身,给领导看 的那些文风,没有扩散能力的八股文,则可以直接停掉——它们都是纸媒时代的产物,如今纸媒都要没了,这些也就没多少意义了,转型是势在必然的。
同时,可以把网络辟谣的工作任务给它,以地方宣传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原有与宣传部门的接口仍然保留。比如宣传部门监测到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流言,它又拿不准,就可以去咨询相关权力机构或者专业机构,然后撰写批驳文字,最后把批驳文和流言一起公布出来。
如果写的有理有据无法反驳,网民就会接受,那些想带节奏的人,也难以带起来。这样的辟谣,不但要说服力强,还要速度。最好是让大多数网民第一次看到这个谣言的时候,是在辟谣的附件中看到的,这样的“预防针”效果会非常好,避免了“先入为主”效应带来的“造谣转发多,辟谣转发少”的窘境。
当然,还需要一些补充规定。比如境外如果有人造谣“某某某领导人如何如何”,这种情况下,你辟谣还公布谣言,那就相当于起到了传播政治谣言的作用。而且这种事也不直接涉及公共事务,对其调查本身也超出了宣传部门的职权范围,也不能境外人士随便编个什么事我们就跟着它的指挥棒转。这部分就可以不视为“社会公众事务信息”,不纳入以上的宣传部门考核,对这类言论及其传播者的处理仍然按照现在的方式即可。另外,涉及到被造谣公民的个人隐私或者人身攻击的,经询问受害者,可以不公布谣言具体内容。
本文指出了目前存在的言论管控方面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解决的思路与初步方案。当然,还是比较粗糙的,仅供抛砖引玉。
但是,即使都按照这样做了,仍然还可能有新的沟通问题。比如政府在辟谣的时候,倒是和相关专业部门沟通了,但是面向公众的时候,说了一堆“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没有xxx的证据”之类的专业内的词语,逻辑上是没有错误,但是群众按照日常语境理解会出现偏差,可能会被官僚作为故意“绕晕你”的工具,这样的沟通只能是做到了“皮”,而没有做到“实”。
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从疫情谈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三篇《把话讲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政府信息发布与社会沟通》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