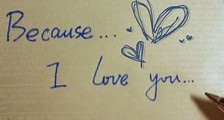东北文艺复兴,谁在复兴?
作者:蒋校长
来源公众号:蒋校长
已获转载授权
“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纵观天下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999年的央视春晚上,来自东北的黑土向全国观众朗诵出这段打油诗。
乐队奏音响起,满堂掌声雷动。
但赵本山心里应该清楚的知道,此时此刻他的老家——东北辽宁,那边的“风景”应该是不太好的。
“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哈哈哈,这词儿整的,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还。”

这段调侃从两个“东北农民”的口中说出,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
而赵本山不知道的是,未来的情况还要更加糟糕。
在即将到来的1999年,全东北的下岗人数达到180万人以上,其中辽宁省占到70万以上。
在这一年的春晚上,还有一个东北人和赵本山一样“没心没肺”。
哈尔滨的黄宏。
在小品《打气儿》中,黄宏用他独有的“慷慨激昂”式表演,扯着脖子喊出一句: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作为总政歌舞团领导的黄宏当然不会下岗,不过在1999年黑龙江下岗的74万国企工人中,应该没几个工人会有像他这么高的觉悟。
下岗,一个颇为沉重的词汇,在全国最高的舞台上,就这样被两个东北人说的戏谑又轻快。
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赵本山和黄宏两个东北老乡侃上两句,几百万的东北工人就能哈哈一笑,丢掉包袱。
也不是刘欢送上一首《从头再来》的激励,丢了铁饭碗的工人就能振奋精神,重新上路。

更多的时候,下岗给当事人带来的唯一感觉,只有痛苦。
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儿子正在读初中,夫妻几乎同时下岗。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要开运动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
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不停的埋怨着。
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杰弗瑞拍摄的沈阳冶炼厂
这是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在沈阳调研时,听当地下岗工人讲的真实故事,他说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
在那段时间里,东北下岗成为了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大问题,全国各地无数人都将目光聚焦到东北,求问着、探索着这片黑土地未来的出路。

这里的人过得好不好?如何才能让这里的人过得更好?
可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永远也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
只有经历者,才有切肤之痛。
而能记录下这一切的人,只有东北人自己。
贰
鲁迅先生讲,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彼时的东北,并不需要悲剧,仅仅需要记录。
因为价值已经被毁灭。
曾是时代先锋的工人阶级,如今沦为陷入泥泞当中的蝼蚁,被逼到时代的角落里。

谁愿意蹲下并靠近这些“弃儿”,真正将镜头对准狼狈的他们呢?
菜鸟导演(严格的讲是摄影师)王兵就这样做了。
1999年年底,他扛着他的摄影机回到了沈阳铁西区。
多年前,他曾经来到位于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学习摄影。
在大厦将倾前最后的辉煌日子里,这座城市的纷繁厚重,还有水泥厂的粉尘与冶金厂的刺鼻味儿,都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铁西区正是沈阳工业的核心基地,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在不到4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诞生出无数个“共和国第一”。

▲ 最让铁西人自豪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上的国徽就是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制造的
第一台大型起重机,第一台H型号万能轧钢机,第一台大容量解体变压机,第一套万伏高压线圈.....
而现在,13万产业工人下岗失业,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

▲ 在沈阳铁西工人村附近的劳动公园或街边林荫道,每天都会有成百上千的下岗工人聚在一起打麻将
王兵决定将镜头对准这些被时代抛弃的人,这些洪流中的落水者,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活的,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在18个月的拍摄时间中,他完全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包括工人们醉酒后怒骂厂领导、光着膀子赌钱、甚至围起来看黄片的场景都得以记录,积累的素材超过300小时。
最终,这300小时的素材被剪成9小时的纪录片,名字叫《铁西区》。

现在在看这部片子,画面模糊粗糙到五米外工人的脸都看不清,没有任何摆拍和情节设计,所有的后期处理只有剪辑,甚至连一段背景音乐都没有。
但工人们的迷茫、压抑、愤怒、不甘、怨念、无助、屈辱还有最后一丝尊严,都被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

在下岗之前的最后两个月里,他们还在破败的厂房里炼着矿,前脚痛骂着领导“妈了个逼的不当回事”,后脚就穿上简陋的防护服去到泄露的铁水前抢险维修。
尽管厂子就要黄了,但有位工人依然在操心,对着镜头替领导们算账:炼一吨铜的纯利润是3000元,一天的产能是300吨,一年开工十个月,净利润也有两个亿。但进的都是黄土,根本卖不出去,那能不赔么?

最让人唏嘘的画面出现在年底的工人聚会上。大家都知道过完年厂子就要被拆除了,所以与其说是联欢会,不如说是散伙饭。
领导致辞讲到改革开放和深圳的喜人成绩时,工人们听完连连鼓掌,激动的好像他们是从中受益的人一样。
工人们轮番提酒,享受着年关岁末的欢愉时刻,借着酒劲和美好的向往,说着“希望永远和同志们在一起”,然后合唱着《走进新时代》。
一个领导在提酒时,平静的说了句“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工人们就一起举杯“干了”。

在艳粉街上,彩票站的员工向路过的工人们兜售彩票:抽烟,伤肺;喝酒,伤胃;歌舞厅消费,太贵;买个彩票,经济又实惠。”
这套顺口的俏皮嗑,他念的嘴皮子飞快,台下的下岗职工们时而大笑时而迟疑。
而谁又能知道,挂着笑脸的卖彩票的他,自己同样也是个下岗工人。

这种割裂的感觉,从始至终的贯穿在《铁西区》当中。
在某些镜头下,他们消极被动又疲惫迟缓,就像是将到强制报废年限的破车,很快被扔进回收站。
在某些镜头下,他们又是如此的朴实执拗,仿佛自己就是工厂的老船长,要与它同生共死淹没在巨浪中。
工人们身上存在的这份割裂感,和时代的宿命无疑的呼应。
曾经创造无数辉煌的是他们,如今带来低下产能和巨额亏损的也是他们,究竟是时代辜负和亏欠了他们,还是他们本就应当被时代淘汰?

可这个中原因,又有谁能说的清呢。
曾经“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最终在改旗易帜的洪流下,沦为棋子一般被丢弃。
王兵评论自己的作品时,说到:
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叁
世纪初年,《卖拐》三部迅速打响了“铁三角”的名气,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这三个东北人以独有“黑土地风味”,将小品这一艺术形式推向新的高峰。
“出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小品王赵本山很快成为东北的新名片。

▲ 借助赵本山个人IP建立起的刘老根大舞台,迅速从东北辐射到全国
当然,反面的批评意见也同样凶猛,很多人抨击赵本山的小品低俗,难登大雅之堂。
“题材全是坑蒙拐骗,语言全是东北土话”。
而这恰恰就是最真实的赵本山,这就是他眼中真实的世界。
这个出生在东北农村,六岁成为孤儿,和瞎子二叔学艺,走街串巷卖艺糊口的人,在根子上就有着与老百姓共情的能力。

▲ 早年的赵本山在街头拉二胡卖艺
一年一段十几分钟的小品并不能满足他的表达欲,他需要一个更大的窗口,讲好“东北故事”与“农村故事”。
2004年1月,赵本山自导自演电视剧《马大帅》。

当时国家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一时之间,很多围绕东北工业之殇及未来发展的影视作品涌现出来。
赵本山则完全从中脱离出来,下岗工人创业发财,亦或是下岗工人艰难度日,这都和他的《马大帅》完全不搭界。
《马大帅》里没有工厂、没有工人,也没有下岗,但却更有力度、更见深刻,更添心酸。

他聚焦的问题是:在东北,一个没有学历,没有技术的农民,进了城以后该如何活下去。
从题材分类和演员表演上来看,《马大帅》是一部喜剧,但把个体放入时代来看,《马大帅》是一部悲剧。
2002年左右的东北小城市,进城的农民到底能干些什么,马大帅和范德彪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厨师、保安、卖艺、算卦、哭丧、护工、婚托、医托、护工、换气罐、蹬三轮、捡垃圾、做人肉沙包......

无法保障的生活,无力寻找的尊严,无处安放的希望。这就是东北农民进城谋生的真实写照。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想打工的农民去工厂的生产线,处处是机会。
而在东北,想打工的农民进城以后,处处碰壁,处处踩雷。
国企垮掉,产业萎缩和产业结构的崩塌导致社会经济环境迅速恶化,即便是民营企业,也没有用人需求吸纳外来劳动力。

他们也有手有脚,更有力肯干,可根本没有工作机会。这才是马大帅们最大的挑战。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生活打趴下。
马大帅开导一时落魄的有钱人,苦口婆心的跟他说:你得支棱起来啊。
范德彪一边碰杯一边给自己打气: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马大帅》第三部的结局是:马大帅和老婆玉芬回到了农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这话用在马大帅和范德彪身上,有点矫情和酸乎,但却再贴切不过。
农村人怀着热望进城,并不能过上好日子,不是你不行,而是时代里就是没有给你留位置。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才是农村人最好的归宿。
和赵本山相比,另一个东北导演的镜头则更加沉重。
来自铁岭的王猛,用了五百万的成本,刻画出一位东北下岗工人无价的尊严。

▲ 《钢的琴》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很直白——工厂里的钢琴
下岗工人陈桂林老婆改嫁给有钱人,回过头来和他争女儿的抚养权。女儿的条件是买一台钢琴就继续跟着他。
在没钱的情况下,如何搞来一台钢琴。
这是一个简单故事,围绕着女儿的愿望和父亲的窘迫展开。
他厚着脸皮开口向工友借钱,发现大家的日子和他一样捉襟见肘;
他在纸板上画出黑白格做出一台哑巴钢琴,女儿摆弄两下就扔到一旁;

他和朋友们喝多了酒去学校偷钢琴,被保安扭送到警察局。
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曾经还算体面的国企工人,他的尊严,他的希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现实残忍的吞噬掉。
在陈桂林陷入困境的同时,旧工厂两根标志性的大烟囱也被决定炸毁,下岗工人们联名写信想要保住那两根烟囱,但没有人搭理他们。
个体的颓唐和时代的落幕悄然呼应。

陈桂林找到了他昔日的工友们,希望大家回到车间里,一起做一台钢琴。
钢琴,钢的琴,用钢铁做的琴。
在彻底被时代抛弃前,一群下岗工人重新集结在车间里开工,打出一台钢琴,为一名父亲守住亲情的希望。
也守住他们最后的尊严。

肆
2006年,是赵本山和他的东北喜剧春风得意的一年。
春晚之上,黑土和白云回到《实话实说》,继续讲述东北故事。

十一黄金周,《乡村爱情》正式在CCTV1播出,并以巨大的优势拿下央视当年的收视率冠军。
到今天为止,《乡村爱情》以差不多一年一部的速度拍到了第12部,成为了本山传媒乃至整个东北文化领域中的“长青IP”。当然,爱情越来越少,变成了东北农村中的百态人情。

从《马大帅》到《乡村爱情》,虽然讲的还是农村的故事,但不再笑中带泪,而是只剩下笑了。
因为一些能发人思考的东西被藏的更深了,甚至让你在笑的时候忘记了思考它们的存在。很多在象牙山村里发生的大事小情,细品之后都颇有深意。
村里男人的“官瘾儿”都异常的大。
谢广坤、刘能、赵四、还有下一辈的赵玉田,都挤破头的想要当村长。

不光是村长,村里随便一个官职都争的不可开交。
谢广坤当上“村委会监事会会长”后,想的是“我得好好整一下刘能这老小子”。
刘能当上“好人理事会会长”,在村里走道顿时“扬巴”起来。
谢广坤最爱开会。

王小蒙进门没多久,就板着个脸在饭桌上说:“小蒙啊,咱们老谢家一直有开家庭会议的传统。”
凡是遇到大事小事,必先开会。谢腾飞走丢了要开会,去豆制品厂找人要开会、刘能生了外孙他也要开会。
但这会根本也不是民主会议,发起人是他自己,发言人是他自己,决策人还是他自己。
村里什么事都能讲的事无巨细,谢广坤骗小蒙买手机演了半集,唯独语焉不详的就是生产发展。

温泉度假山庄游客还没保安多,总经理宋晓峰还总想着扩大规模,让村民五千一万的“众筹入股”。
刘能家里除了种地没有任何营生,大夏天的也没见他下地干过活。
赵四被村里派出去考察,人一走就是几十集,结果子午卯有都没考察出来。
导演想要描绘出东北的新农村生活,很多情节却根本没有跳出东北的旧窠臼。
所有人都想当村官,这是对体制的崇拜和极度向往;
谢广坤天天开会,这是机械而低效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村里人不重生产还从未因经济而发愁,这是“挣多少花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些或多或少的糟粕,究竟是编剧有意想映射什么,还是东北人眼中的“真实世界”,作为观众的我们根本无从而知。

▲ 《乡村爱情2》剧照,前两部还能看到各家劳动的场景,现在几乎再也看不到象牙山人下地干活儿了
赵家班里从底层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二人转演员,在名利双收之后,是否还能继续流淌着“东北农民”的血液,是否还能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俗下去”?
在东北铁锅大炕热腾腾的“俗气”里,艺术旺盛生存的的根源,就在于要有和东北人民共情的能力。

来自齐齐哈尔的梁龙和他的二手玫瑰乐队就是这么做的。
2005年,管虎跑到东北拍了一部《生存之民工》,讲的是东北民工讨薪的故事。
在电视剧的最后一幕,梁龙穿着大花袄,在广阔的原野里唱响了新歌《生存》。
“为何人让人去受罪,为何人为人去流泪”
梁龙一遍遍的呐喊着“命运啊,生存啊”,那边的唢呐一声声的高亢嘹亮起来。

“岁月一年年收获地比醋还酸,幸福像在天上磨磨唧唧不下凡”。再悲伤,再深刻,却又正经不起来,打着哈哈和你戏谑的说出来。
这才是东北人。
再难再累,乐观的东北人是不应该顾影自怜的;再苦再愁,幽默的东北人是不应该伤春悲秋的。
笑着爆粗骂人,讲着段子诉苦。东北人都是“下里巴人的浪漫主义诗人”。
伍
梁龙的摇滚搞了二十年一直不温不火,但另一个搞说唱的东北人去年“整得挺好”。
“有的人表面看起来稳重,背地里已经把野狼disco循环了18遍。”

洗脑的旋律、接地气的歌词、还有“土嗨”的唱腔,经过网络综艺包装之后,《野狼disco》以病毒般的速度迅速蔓延,三个月的时间内播放量突破十亿,成为登顶年度的第一神曲。
真正的一战封神。
33岁的董宝石凭借《野狼disco》单曲走红。

董宝石是吉林长春人,歌迷们更喜欢喊他没红之前的“艺名”——老舅。
在东北,老舅是指最小的舅舅,所谓娘亲舅大,特别是在东北,很多人对老舅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有些时候,老舅和自己是平辈,父母都去上班的时候,半大小子的老舅就是领着一帮孩子疯闹的“孩子王”。

有些时候,老舅又变成了长辈,管他要点零敲碎打的零花钱,考砸了的试卷让他签个字,老师找家长的时候他来顶个包.....
东北人眼中的老舅形象,加上董宝石斑驳的记忆,共同杂糅成董宝石的“老舅人设”。
在走红之前,他出了一张唱片《你的老舅》。

▲ 大学时期的董宝石(左1),成立吾人族乐队
一个人蛮好,但缺点不少,没啥本事,却又好面子的人。同时,这个老舅还总爱追忆往昔的辉煌意象,经济转型前后的辉煌与倔强,如余晖般轮番浮现。
大家都知道那是落日,可老舅总抱有幻想,还以为那是“朝阳”呢。
知乎上的一个热评给老舅打了组标签:四十来岁、下岗工人,开出租车,老婆嫌弃、亲戚埋汰、心比天高....
《浪漫男银》里没钱给媳妇买貂,抬不起头,却在同学会上逞能拼酒,借车换上路虎标充愣;
《夏日发廊》里不得已南下广州,到发廊打工,盘手串、穿人字拖,在珠江边思念故乡。
老舅写这些歌是毫不费力的,就像是老舍写老北京,莫言写高粱地一样,这些东西鲜活的装在他脑子里,什么时候感觉恰逢其时了,就自然的“哗哗往外倒”。

▲ 九十年代的东北迪厅
2018年年底,沈阳人班宇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冬泳》。
在铁轨、工事与大雪的边缘,游走着一些昔日的身影:印厂工人、吊车司机、生疏的赌徒与失业者……他们像一道峰或风,遥远而孤绝地存在。
这些渺小的主人公,勾勒出破败时代下的东北画卷。
这两个八零后东北文艺青年,有着相似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关注的焦点和内心的声音也高度吻合。
老舅不止在一个场合表示,自己认真的阅读了好几遍《冬泳》,很多情节和内容给了他《我的老舅》这部专辑启发。

班宇也表示,他是老舅的歌迷,老舅的每一首歌都是一部小说。他逢人就推荐老舅的旧作《海子》,他认为那是老舅最高水平的作品,唱出时代剧变下的壮阔与苍凉。
时代的剧变,老工业基地出来的老舅当然有这个感知能力。
老舅家在老长春的市中心,红旗街。

长春祖上也是阔过的,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和城市规划,都是老长春殷实的家底,往前扒拉三五十年,长春就是中国第一梯队的城市。
红旗街上工厂林立,最出名的一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就从这里起步。
现在,老厂房改造成了博物馆。空的地卖了,多的人辞了。还有其他的工厂和旧楼,属于那些辉煌的岁月痕迹被齐刷刷的抹去。

▲ 1995年的长春红旗街
仅剩下一条伪满洲国时期的轻轨从红旗街驶过,隔着很久才来一辆红白壳子的电车,慢慢悠悠的,像是怕打扰到这个城市一般。
老舅的歌,离不开这些年代里的回忆,野狼disco里也是如此。
一段蹩脚的“塑料粤语”,大背头、BB机、舞池里的凌凌漆这些上古词汇,小皮裙、大波浪、她的身上太香一串暧昧的元素,几句话讲述出一个夜店搭讪的搞笑故事。
然后“左手画龙,右手彩虹”的蹦迪动作周而复始,再加上无间道、梁朝伟、郭富城,让人梦回到港潮流入内地的黄金年代。

1991年,是《无间道》故事开始的时候。
也是在1991年,德国大众进入中国市场,在长春成立一汽大众合资公司。那正是长春人眼中最好的时代。

▲ 1991年2月6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人们总喜欢安慰别人说:不能总是停下追忆往昔,也不能总是蹲下抚摸伤痕。得站起来往前看,往前跑。
但其实老舅真正想说的是:很多事情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不要忘记。
陆
从2018年年底开始,网络上冒出来一个词——东北文艺复兴。
对标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三杰,网友也选出了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唱歌的董宝石(老舅)、写作的班宇,还有抖音上拍短视频的老四。
去年10月,宝石发了一条微博,他和短视频博主老四一起给《野狼disco》拍mv。
网友很激动,形容这是东北文艺复兴两杰的历史性会面。
宝石也很激动,他说“make 东北 great again”,将东北的文艺复兴。

紧接着在12月的吐槽大会上,宝石和梁龙双双登场,宝石又一次提出了他畅想的“东北文艺复兴”。
梁龙“不乐意”了,他拿话“崩”宝石:
“他说我是他的引路人,我哐哐哐在前面跑,你一边跟着我一边把东北文化复兴了。咋的,东北文化是被我踩塌的啊?”


宝石听了这话笑的不行。
“复兴”、“Again”,这两个词的指向很明确,是破落的大户东山再起,祖上没阔过的人,谈什么再起。
可东北的文艺,何时破落过?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就从长影起步,拍摄的作品和荣获的奖项不计其数;
单田芳最早是鞍山曲艺团的演员,他那部火了四十年的《隋唐演义》,最早就是和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录制并播出的。

单一个哈尔滨少年宫艺术团,都多番承国家汇演任务,周恩来、刘少奇、西哈努克亲王都是台下的观众。
从90年代开始,赵本山、潘长江、黄宏、巩汉林、高秀敏、范伟还有后来的小沈阳、沈腾等,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台柱子,一半都是东北人。
再到后来东北经济不行了,毛宁、那英、孙楠、李健、水木年华活跃在歌坛上,李幼斌、李冰冰、刘烨活跃在影坛上。
这片黑土地上,永远都不缺乏孕育文艺人才的土壤。
东北的文化事业,从来都没有沉沦过。

更多人所关注的、谈论的“东北文艺复兴”,更多的是带着一抹灰色的伤痕色彩。
从上世纪末到今天,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东北从来都没有逃离出那场大变革。
折射到文艺作品的大幕布上,就是下岗大潮带来的创伤与衰退。甚至这一切,都没有逃离出计划经济在这片土地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就像是拉美文学绕不开革命,香港电影离不开黑帮,这片黑土地文艺的灵感与窠臼,就是时代变迁下的计划经济和国企改组。

▲ 沈阳冶炼厂拆迁现场
我们总是喊着“铭记历史”,但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自己的过往岁月被宏大的事业隆隆压过时,很多人都不愿提起或只是唏嘘两声。
然后将那些事情放在心底,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试图开解自己的人: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仿佛历史的车轮碾过的那些沉痛往事,没有人提及,就可以不再存在。

东北的文艺复兴说穿了,是一个有价值的“伪命题”。
说它是伪命题,因为东北的文艺从来都虎虎生风,盛开不败。
说它有价值,因为东北真正的复兴,呼唤的是人的复兴。
那些时代剧变中的落水者,那些在国家快速奔跑中跌倒的掉队者,那些承担国家断臂之痛的普通工人。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他们、解构他们、思考他们、铭记他们,真正有人坚定的去去捍卫他们,东北的文艺复兴才不是流于表面的几首歌、几部剧、几本书、几个人。
否则这场东北文艺复兴,也不过是一场被“炒出”的热点而已,零零星星,来去匆匆。
将上一代人的伤痕化作下一代人乃至下几代人顽强生长的养料,生生不息,哀而不伤,哀而能壮。
这才是东北人的复兴,这也是东北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