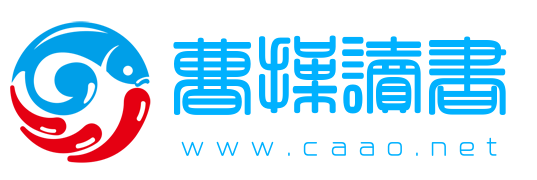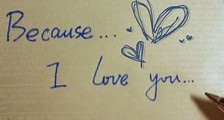中美战略定位的重要细节,藏在这场记者会里
“两会”召开恢复如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记者会却改在3月7日(周日),没有安排在往年的3月8日妇女节。称其“外交男神”的女粉丝们没有收到外长的祝福,会不会有些小失望?我的理解是,没有安排在8日,是不想影响周一工作日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日常发布。当下中外舆论战日趋白热化,需要每天回应被世界关注的中国热点实在太多。
王毅记者会被问的问题也比往年更多。2014年以来的7场王毅记者会,问题从16个增至23个,逐年提升,而2021年猛增至27个,但记者会时间总长却压缩了。往年记者会最长2个小时,这次仅1小时40分钟。同传则用英、法、西、俄、阿、日等七种语言,有史以来语种最多。“高浓缩”、“快节奏”、“国际化”,有的回答甚至只有精辟的几句话,外长记者会细节变化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与世界交往频率的不断加速。

图片来源:新华网
显然,中国外交部必须比过去更高效地处理中外关系,而国际事务观察者们则需要从诸多小细节中品茗中国外交的大变化。比如,王毅提到“云外交”、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中国领事APP,实际上是标志着智能化中国外交的全面启动;王毅自信地讲党是中国外交的“主心骨”、“定盘星”,说明讲好中国故事2.0时代的到来,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再比如,王毅讲述,中国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第一属性”,明确回应西方媒体所谓中国开展“疫苗外交”的猜忌;再比如,王毅推崇延安时代的外媒报道,是呼唤新时代的西方媒体也能出现当年斯诺《红星闪耀中国》般的客观报道,等等。今年的王毅记者会,真可谓“段段有细节,句句显深意”。
对笔者而言,最值得解读的是,王毅在回答每年记者会“必答题”中美关系时,明确讲到“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许多人不一定能感知这句重大表态的微妙之处。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决策层多数时候都回避与美国竞争的话题。这句表态意味着中国已公开明确,自己对美国的全球领衔地位客观上形成了“竞争”,尽管中国主观上可能未必有这个意愿,更希望合作成分更多。
这句表态也意味着中国第一时间回应美国拜登政府在3月3日对华“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新定位。换句话说,如果两国在未来都不认为对方纯粹是伙伴,也不认为对方纯粹是敌人,而更多是居于中间的“竞争对手”角色的话,那么,这样的“竞争者”战略定位意味着什么?中美两国经历了怎样的战略互认进程?中美两国的竞争观有什么不同?中国需要怎样的对美“竞争”?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一)摇摆了20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逐渐清晰
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外部影响变量。冷战结束后,中国对美政策长期坚持扩大积极面,减少消极面,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正确的对美政策,直接为中国争取了长达20年的外部战略机遇期。2012年,中国在16字方针基础上,再次提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后还提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等善意的战略主张。
但这些战略善意没有换来美国相应的对等回报。连续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特朗普执政后软实力急剧下挫的美国精英心存焦虑,将中国的战略善意扭曲成了“争霸野心”。特朗普四年,中美险些陷入新冷战。
事实上,回顾过去20年,21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战略定位“中国是伙伴、对手或是敌人”之间摇摆。
2001年小布什总统刚执政,就提出中国是“潜在战略竞争者”。“911事件”让美国转变看法,视中国为“反恐合作伙伴”。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应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对华采取“对冲(Hedge)”接触政策,意在防范中国的同时,引导中国向着与美国相似体制、被美国规训的方向发展。当时,美国学者一度还提出“G2”、“中美国”的说法,本质是想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大号的日本或英国,成为支撑美国霸权的新兴力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方对华幻想渐渐破灭。中国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增持美债,帮助美国走出危机,可惜,换来的是不是美国的感激,而是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的怀疑、焦虑与恐慌。

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5年,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奥巴马第二任期缓过神后,提出“重返亚洲”等政策,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新强调两国关系的竞争性:“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出现竞争关系”、“须用强势地位管控竞争”。
两年后,特朗普总统上台,直接把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要与中国开展一场全面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此后,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开打。被讥为“史上最差国务卿”蓬佩奥,甚至直接称中国为“美国最大敌人”,明确要与中国打“新冷战”。
从拜登总统上台的40多天看,特朗普对华压制策略并没有被完全颠覆。2021年3月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讲,列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任务,直接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同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美国主要竞争对手。至此,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与摇摆,而是直接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
不过,面对这个“头号竞争对手”的新帽子,中国有理由保持战略自信。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犹如中国国运亨通似地,为中国创造了综合国力接近美国的战略契机以及对全球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以至于拜登执政后,在除夕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在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都表示,无意与中国发动新冷战。布林肯也强调,与中国“能合作时还是会合作”。这至少说明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被蓬佩奥带偏,不敢、不愿、也做不到把中国定位为“敌人”。
问题在于,经过20年的接触、琢磨、博弈、摩擦甚至低烈度的冲突与较量,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伙伴”,也还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而是逐渐明确了对中国“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那么,中国需要尽快给予怎样的回应呢?这正是笔者在2021年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记者会中笔者感知到的一些端倪。
(二)“竞争”,不完全是坏事
特朗普对华打压的四年,对中国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没有科技打压,中国不会那么重视“卡脖子”科研短板;没有贸易打压,中国不会那么切实地感知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意义;没有签证打压,中国也不会那么强烈意识到高端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新冷战威胁,中国更不会那么坚决地放弃对美国的幻想。
现在,是重新务实地思考对美战略的时候了。
其实,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一直在努力。2018年记者会时,面对彭博社关于特朗普对华攻击性的评价时的提问,王毅就坦言:“如果说中美之间有竞争的话,那也应该是良性和积极的竞争。”
2020年7月9日,笔者所在智库与相关机构承办“中美智库与媒体视频论坛”,王毅出席致辞,罕见地发表系统性的对美政策讲话,呼吁美国“拨乱反正、重回正轨”,建议两国“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重申“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我们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呼吁“走对话合作之路”,还创造性地提出“三份清单”(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
那次讲话,笔者在场聆听,印象最深刻地还有一句:“有人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视历史另起炉灶,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强行脱钩,而是应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承认“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
2021年2月22日,笔者所在智库与相关机构再次承办“蓝厅论坛”,王毅对美国新任政府喊话,重申“相互尊重”、“加强对话”、“相同而行”等一贯主张之外,还铿锵有力地提出“相互尊重”的具体条件,即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同样,美国应“美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要有“三个停止”,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这场讲话,笔者也在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句,即“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很显然,外交决策者在深思熟虑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战略新定位。
3月7日,王毅在记者会中强调“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这又比过去进了一步。王毅公开用“良性竞争”一词,印象中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战略自信进一步提升。
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1月25日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就强调,“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如果追溯,早在2004年5月1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就曾自信写道:“机遇总是垂青勇于竞争的人”。此后还反复讲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习近平的这些讲述或许可以引申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竞争观”。
在英语语境中,“竞争”不是什么坏事。衡量两国的关系至少可分为5个“C”,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冲突(Conflict)。“竞争”居中,显“中性”。
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更有底气,不必谈“对美竞争”而色变,更不必一谈到“竞争”,就往战略对抗、冲突的方向去推论、去联想。要知道,同学、同事、兄弟姐妹之间都可能有竞争,奥林匹克精神内核之一也是“竞争”。
竞争有激烈的力争上游,竞争也不排斥相互敬重,竞争更不排除合作共生。竞争是人间常态,关键在于,怎么样的竞争?这才是未来中国对美外交以及全球布局需要重点思考与全面践行的工作。
(三)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国竞争?
改革开放的40多年,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的20年,中国经济、贸易、金融、产业、文化能在全球层面呈现崛起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正视国际竞争,拥抱国际竞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向对手学习,并在一些领域实现赶超,在另一些领域共同提升。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残酷,并不在于竞争的存在,而在于当霸权国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竞争规则,并成为世界的通行标准时,小国不得不被迫服从。
40年来,中国没有寻求颠覆他国政权,没有出兵干预或胁迫他国内政,没有带给世界战争、冲突、难民或任何大规模的人为灾难。相反,靠着勤劳、智慧,为世界输送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建设实用可靠的路桥塔港,致力于解决贫困、文盲等人类痼疾。中国走的恰恰是不一样的国际竞争道路。由此看,即使未来中国真正采用所谓“对美竞争”的战略定位,也不会排斥“与美合作”。中国走的不是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是欺压他国的邪路,而是寻求新的大国良性竞争之路。
笔者看来,所谓“新大国竞争”,至少包含四类:
一是楷模之争:比哪个国家在国内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解决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哪个国家更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可复制的经验。
二是合作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道义感召,推动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普及、复苏经济、科技创新、削除贫困、维护治安、帮扶弱者等等。
三是红利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的增量,为全球和平稳定提供更多贡献。
四是视野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是良性竞争、公平竞争,中国没有理由去拒绝、逃避或害怕。70多年前,以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大国协调核心的联合国宪章设立,本身就是力求创造比19世纪、20世纪初更先进的大国竞争文明。未来的中美竞争,理应比过去任何一组大国竞争更文明、更体现人类的进步性。
当下的难题在于,如果美国总有一批人那么野蛮、霸道、恶劣、使阴招,中国怎么办?笔者的建议是,中国应该效仿美国在国务院、国防部等设立“中国工作组”那样,在各个关键部委设立“美国工作组”,全力应对外部这个最大的影响变量。
笔者相信,“绝对贫困”这个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内变量都能解决,只要专心去应对,“美国压制”这个外部变量,也应该有信心处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