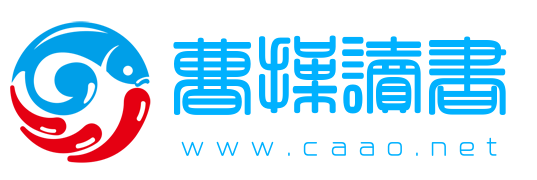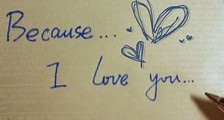猛哥:再见了,“小镇青年”傅高义
作者 :爱你我的猎物 2020-12-22 18:11:46 审稿人 : admin
1961年,EzraF.Vogel 决定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
Vogel是德语姓氏,中文发音近似“傅高”,Ezra则被翻译成“义”字,因该字“意味着很高的道德标准”。
傅高义说自己很幸运,“在美国顺利完成学业,成为著名学者,是美国学术界唯一对日本和中国都具影响力的亚洲问题专家”。
作为犹太人,其实他的起点不高,还差点被希特勒给祸祸了。
感谢他爷爷和父亲的果敢,二战前夕从波兰跑到美国,才不至于像留在波兰的亲属那样遭到纳粹迫害。
1930年7月,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小镇特拉华,长大后就读于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学。“这所大学很小,但是我对它很有感情。”
终其一生,傅高义都透着彻底的质朴,对此他并不讳言,很多年后他与费正清双峰并峙,就笑称,“费正清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社会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而我是小镇长大的青年。”
1950年,傅高义从威斯理安大学毕业,这所大学不仅塑造了他的气质,还影响了他的研究风格。“我在家乡的小镇上学的时候,一位老教授告诉我,你写东西的时候,应该学会讲故事,不管内容有多复杂,都要写成普通人能够读懂、同时有知识的人也会有兴趣的故事。那时候我很年轻,但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
2
服过两年兵役后,傅高义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
1957年,他博士毕业,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如此告诫:如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1958年,28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和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第一年学习日语,第二年开始做田野调查。
他选择田野地“真间町”(Mama-cho)是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行政区(郭沫若和他的日裔妻儿曾在此居住过),后来出书时,为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改为“M町”(Mamachi)。
傅高义本要对孩子情绪失调的家庭和孩子健康的家庭做比较研究,但发现“情绪失调的孩子成了父母关系严重紧张的替罪羊”,这与美国别无二致。相反,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工薪雇员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家庭模式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间的关联”。
当地小学校长给傅高义挑选了六个家庭,这些家庭的丈夫们大都是工薪雇员,每天通勤去东京上班。一年的时间内,傅高义每周都要对6个家庭进行访谈。
几年后,傅高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日本新兴中产阶级》,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傅高义在后记中写:“我一直对几位人类学教授的告诫深信不疑,他们说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日本新中产阶级》堪称文化人类学的典范,自该书第一版出版以来,来自东京不同郊区的人都问傅高义,研究的是否是他们的社区。
3
返回美国的傅高义最初在耶鲁大学任教。1960年11月,他到哈佛大学探友,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问他是否愿意研究中国: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
彼时,麦卡锡主义逐渐失势,美国意识中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对手长期存在,曾作为“危险领域”的中国研究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可当时的情况是,“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
傅高义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当时,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想扩大中国的研究,他们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
1961年,在费正清的提携下,傅高义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返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去世后,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他跟随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学习中文。
这位立志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人,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傅高义。恰如其名,他在学业上“有很高的道德标准”。
4
1969年,WG还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大洋彼岸,一本名为《共产主义下的广州》问世。作者正是傅高义。
费正清称之“将成为社会学家们如何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
此后,很多其他美国学者就照着傅高义研究广州的方式,研究北京、上海或者中国其他一些城市。比如罗威廉研究汉口的系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是罗威廉继《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写作过程堪称神奇,因为傅高义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广州实地调研。“当时我没有办法去大陆做研究,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封闭的。有人选择去台湾,但我觉得台湾对大陆肯定有偏见,相比之下,香港会客观一些。另外,在香港做研究有一个好处是,当时有很多人偷渡到了香港,他们带来的内地消息会多一点,所以香港是个相对好的选择。”
1963年,傅高义在香港住了一年,他约谈了大量来自广东的移民或偷渡客,系统阅读《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一年后回到美国,继续阅读哈佛大学所购的1949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
他原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
两年多时间内,傅高义老老实实每天读报纸,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研究的对象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冷静地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做出观察和分析。“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他日后观察和评介中国的原则。
5
1973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东亚中心退休,傅高义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同年,傅高义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他通过香港来到深圳,等待几个小时后,在罗湖火车站登上去往广州的火车,趁机在广州小住几天,虽然尚未得到在中国研究的机会,但他去看了佛山南海平洲人民公社,没有电视,只有很小的电灯。
傅高义对广州的观察特别有意思:“广州人有一致的思想、感情模式,这一模式源于他们长期的商业传统。广州人是善于处于世俗事务的人,精明的讨价还价者,长于技术,批评直率,勇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个人主义者,而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尽力而为的有组织的人。因此上海成了大型工商企业的中心,而广州仍然是独立的小商人、小手艺人的大本营。”
没有溢美之词,但1987年,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来到广东,系统研究广东的经济发展与改革。
对于写作目的,他心知肚明,“他们希望外国人到广东投资,但当时广东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省里领导们认为,中国人写的书国外会当成是宣传不会相信,如果一个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可能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就像我以前写的《日本第一》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日本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广东做研究,觉得如果能写成一本书,对广东也有一定好处。”
傅高义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我还告诉他们,我不是埃德加·斯诺——他是一个记者,他到延安,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泽东在做的事情;我是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评。他们说可以,他们觉得写基本的情况能让外国人客观地了解广东,他们对此很乐观。”
当时广东省经委为他派了个年轻干部做助手,这位叫“小窦”的人后来变成了傅高义的朋友。
在近7个月的时间内,傅高义走访广东全省14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100个县中的70多个。“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的很多细节,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
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
20年,两本书,傅高义写就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让他觉得稍有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R,不过他与R家结下了缘分。
后来,R的孙子在哈佛大学读书,成为他写总设计师传记的助手。
6
1995年夏,傅高义再次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 ,他决心改变中心以往只关注学术,而对与国家、政治、商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合作缺乏兴趣的传统。
1997年11月1日,他促成了长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若干年后,傅高义要写总设计师的传记,长者还特意给了一个小时接受访谈。
那是2000年夏天,即将从哈佛大学退休的傅高义想写一本关于总设计师的书,“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傅高义从未与总设计师会面。他们最接近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为两个国家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由于音响状况不尽如人意,傅高义完全听不清总设计师在说什么。
傅高义只得一头扎进文献资料里。平均每天不少于10小时。为此,他又开始强化他的汉语学习,每周二、四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去的女老师学习中文。
在研读文献之外,他还总共花了大约12个月在中国。他见到了总设计师的女儿们,但没能见到总设计师的儿子们以及秘书。
此外,他还去了一些地方,比如山西太行,四川广安、江西瑞金和南昌等。
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后,傅高义这样概括总设计师的性格特点:“思考大事,把握大方向,小事让别人干。”
2013年1月1日,《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出版。获得包括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文化特殊贡献奖”,
在美国,有记者批评傅高义掺杂了个人情绪,“当然因为我个人对中国有好感,希望中国成功,即便如此,我也会有批评———尽可能地写全面的情况,这是我的目标。了解大局,考虑大局,客观分析,这是我做为一个社会学者的立场。当然人的性格要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着眼大局。“
《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暗示,傅高义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接受删节,从而使之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随后,威斯理安大学校长给该报写信说,此书在中国出版之前,傅高义就与该校签下协议,将中文版的全部版税捐赠给自己的母校。《纽约时报》后来刊登了这封来信。
人如其名,这个老头儿可真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呢。
7
虽然在西方享誉半个多世纪,直到2013年,83岁的傅高义才被中国大众熟悉。
此后,每逢中美关系起波澜,中国媒体都会习惯性问道于他。而他的回答永远不变,那就是中美必须合作。
对于特朗普,他的评价甚低。其实他们颇有纠葛。
1975年,傅高义从日本基金会得到一笔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关于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受到空前欢迎。
《日本第一》影响了很多美国青年对后进国家的认知,认为这些国家是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必须反击。
其中一人尤为激烈,思想一以贯之。1987年他自费在《纽约时报》发布意见广告抨击日本,呼吁美国提高对日关税;1988年在奥普拉的节目上骂日本“跑来美国卖车、卖录像机,打垮我们的公司”;1990年他接受《花花公子》杂志专访时说:“日本人赚饱我们的钱,买下整个曼哈顿。”日本地产泡沫破灭,经济陷入滞涨后,他又把矛头对准新崛起的中国。2016年他当选为美国总统。
此人就是特朗普。
无独有偶,在中国其实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
据《日本新中产阶级》的注释,傅高义曾兴致勃勃地回忆,“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Z带队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听众里有人向Z提问:‘你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Z答道:‘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去问傅高义啊!’言毕,底下一片大笑。Z不解,问大家为什么笑,有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傅高义曾说:“Z是个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再有机会写一本书的话,你会写谁?我回答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会写Z。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再写他的书了。”
天不假年。遗憾的是,他拟为另一个中国前领导人H写书的计划也永远搁浅了。
2020年12月21日,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中日近现代史研究者沙青青说,傅高义的去世,代表着自费正清时代以来美国那辈东亚学研究者时代的最终谢幕。“这批人不仅是学者,也是战后美国对东亚政策制定的实际参与者与见证者。在如今这个时间点,傅高义的去世更具象征意义。”
在线下载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