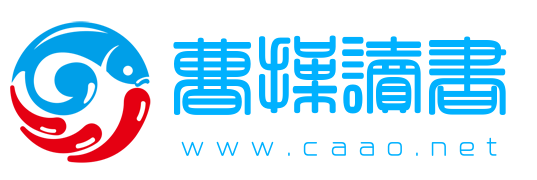剑道征途笔趣阁版
书籍简介

杨如海是个老刽子手,这职业下贱且不祥,久染秽气的他在走夜路的时候,遇上了个不会说话的绝色哑女,便将其带回家中,昼夜贪欢,殊不知,那哑女不是人……杨如海因心慈结缘怪道,得了柄宝刀,叫做碧落,又收养了个孤儿,起名陈天赐。陈天赐二十岁的时候,代替杨如海去处决犯人火王燎…
内容简介
杨如海是个老刽子手,这职业下贱且不祥,久染秽气的他在走夜路的时候,遇上了个不会说话的绝色哑女,便将其带回家中,昼夜贪欢,殊不知,那哑女不是人……杨如海因心慈结缘怪道,得了柄宝刀,叫做碧落,又收养了个孤儿,起名陈天赐。陈天赐二十岁的时候,代替杨如海去处决犯人火王燎…
内容在线试读
这天上午,杨如海叫来正在操刀砍木头人的陈天赐:“别砍了,过来!”
陈天赐跑到杨如海跟前:“师父。”
杨如海说:“从今往后,不用砍木头人了,可以砍真人的头了。”
陈天赐愕然:“啊?!”
杨如海道:“今天,咱们永乐城要处决一批死刑犯,我跟监斩官打过了招呼,由你代替我去行刑。”
陈天赐吃了一惊:“我去?”
“你去怎么了?”杨如海把眼睛一瞪,说:“你都多大了,该动动刀子,杀杀人了!过来,到宝刀底下磕头!”
陈天赐咽了口唾沫,嗫嚅道:“是,师父。”
堂上供奉的是一把湛蓝如天的大刀,陈天赐从来都觉得这把刀稀奇,一来颜色少见,二来笨拙沉重。但杨如海却不止一次对他讲起过这把刀的来历——杨如海说这把刀是一柄宝刀,名字叫做“碧落”,是一位道行极深的高人赠送于他的,还救过他的命。
原来,在许多年前,杨如海夜里喝了酒,微醺中晃晃荡荡的回家,忽然间瞧见了一个浑身素裹的女人坐在路边,哭得泣不成声。
杨如海是个刽子手。刽子手以杀人砍头为生,人人都说这种人赚的钱不干不净,做的事缺仁缺德,生前必受报应,死后必下地狱,所以极少有媒人会为刽子手提亲,更极少有女人愿意嫁给刽子手,都觉得秽气。
所以,杨如海便是大光棍一个,虽然待遇丰厚,酒肉无忧,但始终缺个知冷知热的床头人,因此他最眼馋的便是女人。
杨如海带着酒意,趁着月光,瞧那哭泣的女人,见她脖颈白皙,面容娇美,身段丰腴,十分的动人,不觉就咽了口吐沫,搓了搓手,上前去问:“大妹子?”
女人抬头看杨如海,杨如海嗅到一股味儿,越发的神魂颠倒,问道:“大妹子是哪里人?夜里怎
的不回家?哭什么呢?”
那女人只是抬头看着杨如海,并不说话,身上的气味越发的往杨如海鼻孔里钻,杨如海更是心痒难搔,反复问了几遍,那女人仍然是不做一声,却也不怎么害怕,哭声倒是渐渐的止住了,杨如海有些恍然,暗忖道:“八成是遇上了个哑巴。”便问道:“你莫不是个哑巴?被人给嫌弃不要了?”
那女人怔怔的看着杨如海,杨如海便真以为她是个哑巴,说道:“我是个刽子手,你要是不觉得秽气,就跟我回家过日子,保你穿衣吃饭,怎么样?”
杨如海伸手去拉她,她也不拒绝,也不反抗,跟着杨如海就走了。
回到家中,带到卧室,脱鞋褪掉衣服,那女人始终没有抗拒,杨如海才初尝人事。软被厚褥里,如痴如醉,欲仙欲死,从此如获至宝,把那女人当做心肝儿一样,养在家里,日日夜夜闲暇得空时,就要“例行公事”,从不觉得倦怠厌烦。
如此这般,过了一个月,杨如海渐渐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头晕眼花,有时候竟然连自己用熟了的刀都拿捏不稳了,做那事儿也大不如从前。
哑女虽然不嫌弃,也说不出话来,但是杨如海自己却有些不好意思。寻思着听人说起过,久行房事必定虚亏,便琢磨着去城里找个郎中,开几副药来吃,调养调养,总之,自己天仙似的女人是不能怠慢了。
那天,杨如海拖拖拉拉的出门,去生药铺里找郎中。走到半道里,忽然瞧见了一个道人,衣袍破败,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躺在一块大青石板子上,赤着脚,露着腿,蜷缩着身子,口中“呼呼”,正自大睡。
此时正值深秋时节,风寒天凉,杨如海见那道人衣不蔽体,又睡在石头上,十分的可怜,心中便生了怜悯之意,就解了自己的衣袍,披在
了那邋遢道人的身上。
那邋遢道人“吭哧”一声,却在睡梦中一脚把杨如海刚皮上去的衣服给踢掉了。
杨如海虽然刽子手,却是好脾气,又捡起来衣袍,给那邋遢道人重新披上。
可是那邋遢道人就像是故意似的,又蹬腿把衣袍给踢掉,杨如海不觉笑了笑,又捡起来给他披上。
如此这般,一连三次,那邋遢道人突然坐了起来,盯着杨如海“嘿嘿”直笑,露出满口的白牙。
杨如海道:“原来是个傻子。”
那邋遢道人敛住了笑容,一双眼睛忽然变得晶亮晶亮,说:“自己傻到命都快丢了,反而还说别人是傻子。”
杨如海一怔,问道:“你是说我?”
那邋遢道人说:“你还记得我吗?”
陈天赐跪在碧落底下,虔诚的焚香,叩拜,磕了八个响头。
陈天赐是杨如海的弟子,是杨如海从小养到大的弟子,几乎可以算作是杨如海的儿子。
所以,近乎子承父业,杨如海是刽子手,陈天赐自然也要做刽子手。
刽子手这种职业,是下九流之一,与娼妓、戏子、师爷、神棍类似,极为人瞧不起,人们常说只有长得丑恶、品行不端的人才会去做刽子手,所做之事耗损阴德,断子绝孙。
其实杨如海长得并不丑,也不凶恶,陈天赐长得就更不丑,更不凶恶了。
刽子手的薪酬是很高的,除了薪酬,往往还会有犯人家属送上红包,求他们动作利索,不要让犯人临死前还吃苦——杨如海刀法精准,绝不收犯人家属的红包,从来都是一击毙命,给犯人来的痛快,越是如此,越是有人上红包给他。
一般的刽子手,拿了薪酬之后,都爱吃喝嫖赌,毕竟很难成家,只能图乐,而杨如海在经历了獭怪的事情后,对女人算是绝了念想。念及那道士的好处,杨如海每每在拿了薪酬以后,便去周济穷人,在家里也吃斋,不沾酒肉,以积阴德。
可见,杨如海的品行也不算不端,只不过,他确实没有讨来媳妇,没有后嗣,算是断子绝孙了。
陈天赐在不到一岁的时候,被亲生父母给抛弃了,就丢在了杨如海的家门口,杨如海瞧见了,眼见可爱灵动,就抱回了家里,看着孩子,杨如海有说不出的欢喜,认为这孩子是天赐的礼物,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做“天赐。”
至于姓氏,陈天赐被抛弃的时候,有块被褥包裹着,里面有张字条,写了陈天赐的生辰八字,也写了他姓“陈”,于是就叫做陈天赐。
陈天赐的身世,杨如海没有瞒着,打小就告诉了他。所以也不让陈天赐叫自己“父亲”,而是叫“师父”。
陈天赐跟着杨如海,学不来别的本事,除了刀法——杀人砍头的刀法。
今天是陈天赐二十岁生辰,杨如海恰又接了公务,官府指定由他来砍一个穷凶极恶之徒的脑袋。杨如海倒是不以为
意,跟监斩官打了招呼,说自己徒弟是时候出师了,要让陈天赐去代替自己行刑。监斩官不同意,杨如海奉上一个红包,监斩官笑纳之余,自然改口同意。
在陈天赐出门的时候,杨如海还特意交待道:“天赐,记好了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砍头的时候,看准了落刀处,就立刻下手,不要犹豫!收工以后直接就走,不能回头!判斩刑的人怨气很大,死后必生冤魂,你要是回头,元气就会被死人的冤魂给勾走了!”
陈天赐点点头,表示记住了。
杨如海又说:“收工以后,到了公门里向上官汇报交差的时候,要让衙役多打你几下板子,驱走秽气!打的皮开肉绽也不要喊疼,回来我给你敷药!”
陈天赐又点点头,说:“我记住了,师父。”
陈天赐要走,杨如海又喊住他,说:“听说你要砍的那个犯人穷凶极恶,你怕不怕?”
陈天赐挺直了胸膛:“不怕!”
“去吧!”看着陈天赐远去的背影,杨如海摇了摇头,道:“这孩子,从小教他杨家祖传的刀法,招式全都学会了,但是体内的气,却是一点也没有凝聚成功。唉……可能跟我一样,天生就是废料,只能做个刽子手了。”
原来,杨如海的远祖是位玄门中修炼古武玄术的绝顶高手,在凡夫俗子眼中,如同神人般的存在。只可惜,想要修炼玄门玄术,不但需要聪慧过人,还需要躯体的资质过人。脑子聪慧,能可以悟透玄术,躯体资质过人,能够凝练玄气,玄气和玄术决定了玄门修行者的道行高低!
杨如海的身体资质就是一般,很难凝聚玄气,因此并没有学到祖上本事中十分之一,他传授陈天赐的时候,也发现陈天赐无法凝聚玄气,身体资质似乎比自己还差,不禁感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且不说杨如海,还说陈天赐,他嘴里说是不怕,但是在去刑场的路上,陈天赐就开始有些紧张了。
他一路低着头走,心中反复的想自己要砍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冷不防撞上一人,满鼻子幽香,定睛一看,见是
个目中含烟带水俏生生天仙似的姑娘,不由得痴了一痴,脸早就红了,正呐呐的想说声:“对不住。”旁边早有一个短须男人劈手朝他抓来,喝道:“走路不长眼睛么!?”
那天仙似的姑娘说道:“没事,不要为难人家。”
那短须男人狠狠的瞪了陈天赐一眼,和那天仙似的姑娘快步去了。
陈天赐目视着那姑娘的背影,心中暗忖道:“师父常说,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是不能招惹,尤其是不能和她们睡觉,因为会被吃掉。呃……”
胡思乱想了片刻,陈天赐觉得被这美人吃掉的感觉应该也还不错,然后又朝刑场上走去。
到了刑场上的时候,陈天赐开始哆嗦起来,他并不胆小,只是怯场。杀鸡宰鹅虽然难,学学也就会了,杀人这种事情,即便是学了,也未必会,即便是会,也未必敢,更何况,陈天赐平时练得都是砍木头人。
这一次要处决一批犯人,都是造反的贼人,一共有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每一个都来头不小。尤其是陈天赐要砍的那个人,他比另外那十个人加一起还要来头大,这个人叫做燎原。
燎原听起来像是个号,不是名字,但他真正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他原本姓钟,叫平生,可现在,人们只知道他是燎原,火王燎原!
这四个字,一听就威风霸道的很,可是跪在刑场上的燎原却一点也不威风霸道。
跪在刑场上的燎原狼狈异常——他的琵琶骨被一条很粗的铁索穿着,他的泥丸宫上还贴着一张金光灿灿的金符,他的手腕上、脚踝上也都锁着精钢打造的镣铐,全都又粗又长!
这也正说明了燎原的本事太高,不这样对付他,恐怕会让他逃走。
燎原虽然很狼狈,但是气势还是很足,他跪在那里,却仍然挺直了腰板,目光亮如闪电,整个人威武如同雄狮。
陈天赐本来就发憷,瞧见了这样的人,瞧见了这样的阵势,更加有些不安。
午时三刻快到了,监斩官喝道:“预备行刑!”
十一个刽子手,连同陈天赐在内,都齐刷刷的举起了大刀,看准了
犯人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