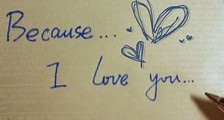乌鸦校尉:“优待”英国女婿,到底给了谁一记耳光?
作者 :你爱我还是碍我 2020-03-24 20:25:32 审稿人 : admin
说得是外国人和本国人在中国都受到了差别对待。
最近沸沸扬扬的英国女婿事件,就为我们生动地演绎了什么是“超国民待遇”。
一位辗转多个国家的英国籍女婿,在回到上海自己的小区后,感受到了如沐春风般的关照。
按照当时上海的入境居家隔离政策:「一户一人」或「一户一家」,这位英国籍女婿是必须要集中隔离的。
当然,也有人说,这位女婿是满足了“可以居家隔离”的条件的。
但无论他究竟满不满足条件,他的丈母娘和妻子都希望他能去集中隔离,因为妻子生了孩子,才两个月大。
但他不肯听,街道办和社区带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劝说,他还是不接受。
在劝告无效后,社区并没有动用行政手段强制执行,也没有因为这个他在几个高风险国家逗留,而对他高度警惕。
社区竟然另辟蹊径,让这位外国女婿的老婆全家搬到亲戚家,让洋女婿自己在家里住。
这份暖心关怀实在是令外国人很动容,让国人听了很愤怒。
环球时报的胡主编也“坚决给这个故事打0分”。
就洋女婿这个不听劝的态度,换成国人,别的不多说,长时间的沟通是绝对没有的,不听话就强制隔离,哪有那么多借口?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某些官员真的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老百姓早就站起来了,他们还在搞“对外国人唯唯诺诺,对国人重拳出击”。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简单的差别对待现象,但反映的却是有一大批人,在民族精神自我矮化的惯性。
中国现在国力仅次于美国,你崇拜一下美国也就算了,什么半殖民地状态的日本、早就衰落了的老牌流氓英国,也要崇拜,乃至与是个外国人,就要对其毕恭毕敬,傻不傻呀?
我们有很多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大学师生,这种思想上的余毒就是没有洗清,误人误己。
前两天就有一个华裔留学生在推特上发视频,她声称新冠是“武汉病毒”,是从中国传到全世界的,还代表中国向全世界道歉。
不仅道歉,她还表示,自己恨中国人远胜于其他人,希望中国人从美国滚回去。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脑子里就有这种思想,显然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们去纠结于一两件事的对错,其实不触及根本,这些事情根本上都是一个思想问题,需要文化界艺术界的努力。
为什么?
因为欧美国家之所以在舆论场上有这种远远超过国家实力的话语权优势,就是利用艺术界和文化界的人,花了很长时间打造出来的。
美国没有文化部,也没有宣传部。但美国的情报机构承担了宣传的作用。
当年的“对苏宝具”、“遏制战略”提出者、冷战“设计师”乔治·坎南就直言不讳:
“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苏联的全盛时期,苏联妇女地位比欧美更高,也比欧美更早有选票,苏联高举“民主”大旗,其意识形态的确对美国想要领导的“自由世界”产生了动摇。
苏联的宣传部门深入欧洲,不仅在欧洲的青年群体中培养出了不少对共产主义感情深厚的青年,就是美国自己内部,也有不少人对其心向往之。
于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CIA)出手了。
别以为CIA只会简单粗暴的暗杀、颠覆,他们的“活”可以干得很文艺。
正如美国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所言:
“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
“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1950年,CIA在欧洲操纵成立了一个“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资金则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这几千万美元本来就是“援助欧洲”的钱。
“文化自由大会”不差钱到什么程度?CIA的人自己说“我们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账,真是不可思议”。入会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可以拿到丰厚的报酬。
这个大会在文化宣传上光鲜亮丽,但中情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前始终没有暴露。
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全职雇员有几十位,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
这个庞大的组织,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纳博科夫领导,实际上统归由一个CIA特工乔斯尔森直接指挥。
奖励艺术家是有技巧的,艺术作品到了一定的水平,剩下的评价都是很主观的,CIA就挑选出比较亲美反共的作品进行颁奖。
比如吉拉斯的《新阶级》、艾略特的《荒原》、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等;
更有甚者,原本不是“纯粹”亲苏反美的作品,中情局也会想尽办法让它变得“纯粹”,大名鼎鼎的奥威尔,其《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优秀作品。
奥威尔本人经历过苏联的大清洗,自己的“苏联梦”有过幻灭;也因为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被英国军情五处长期监视,所以他对两种意识形态都很抵触。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是极权化的政权,都是他讽刺的对象,他个人偏向比较理想化的民主社会主义。
但西方在作者死后对原著进行电影改编时,故意扭曲原意,将《动物庄园》原著中代表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删除,只留下了象征社会主义苏联的猪,成功把对全人类的反思,引导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抹黑。
直面苏联,他们则专挑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苏联作家的作品,鼎力相助。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日瓦戈医生的遭遇,表现了俄国两次革命和两次战争期间偏残酷和毁灭的一面。
中情局特工直接建议:
“要最大限度地出版各语言版本的《日瓦戈医生》,以求最大限度地在自由世界发行与喝彩,并考虑促成诺贝尔奖这样的荣誉。”
在其全力保驾护航之下,帕斯捷尔纳克成功拿下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只是榨取该书价值的开始。CIA第二年4月便出台了行动指南,指导各地特务如何鼓励西方赴苏“游客”与当地人谈文学,谈《日瓦戈医生》。
冷战结束后多年,CIA相关档案有大批解密。
英国女编辑桑德丝写了一本《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揭露美国情报系统操纵的“文化冷战”是如何运行的。
当然,CIA如今早已“完成任务”,用不着避讳什么,可以直接把桑德丝书的相关内容的直接放自己官网上。
美国的“影子文化部”中情局这些以文学、艺术为幌子的大费周章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他们在苏联培育除了一大批“反共精英”。
这些人因为头顶各种奖项的光环,成为了不少人的意见领袖,带头拆墙。
普通人受到他们的作品影响,慢慢潜移默化就具有了同样的思想。
直到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在欧美的媒体上被冷落,欧美人开始给中国的某些人发奖了,他们才终于幡然悔悟。
写作《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我们就不再赘述,毕竟他真的被流放去古拉格监狱待过,而且后期立场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重新称赞他原本讨厌的斯大林,勉强算实事求是。
季诺维耶夫,苏联最著名的异议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自己是苏共党员,却扛着红旗反红旗,鼓吹绝对化自由主义、猛烈抨击共产主义制度和苏联社会。
1978年,他被开除党籍、驱逐出境,他在被驱逐出境的当年还非常硬气地表示:“即使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书要我付出生命作为代价,我也绝不会停笔。”
接受了社会的毒打之后,他晚年回到俄罗斯,转而抨击西方化之弊,大声疾呼珍视苏维埃优秀的价值观念,重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俄罗斯只有在恢复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复兴”。
他甚至忘了当年的“绝不停笔”的flag,马上真香:
“假如我当初知道我写的东西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宁肯砍下自己的双手。”
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他在国外创办的《大陆》杂志,被认为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鲜明的刊物。
他成立“抵抗国际”反共组织,多次自称“坚定的反共分子”,西方当然也“尊”他为“反共斗士”。
而在苏联解体后,他的思想剧变,1994年,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的他(1995年去世),对《真理报》记者谈到: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
“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女诗人德鲁宁娜,在苏联解体前的军事政变“八·一九事件”时,她还专程赶到白宫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她觉得叶利钦是“正义与善”的体现者,认为在白宫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
但解体后她很快发现,一切都不是应有的样子,周围的生活难以忍受,目睹国内出现的混乱状态,她终于意识到了俄罗斯将会有怎样悲惨的前途和命运。
三个月后,她服安眠药自杀。
自杀前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她极度担心没有人能在“悬岩边上拉住罗斯”使之不掉下深渊,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热衷批判苏联制度,支持“改革”。
但苏联解体后,他发现物价飞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更有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领养老金者的打击和剥夺。他转而认为“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
思想上的苦闷,加上晚年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身体有病,最后他选择在家里开枪自杀……
当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同样没有抵抗住这种侵蚀。
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拍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河殇》。
从第一集开篇翻滚的黄河画面开始,作者反复地强调一个结论,那就是“黄河文明”必将终结和消亡,人类会迎来“蓝色文明”的曙光。
一些似是而非看上去诗意,实际令人作呕的台词,不断轰炸着面前的观众:
“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同时,作者还将“黄水”、“黄土”、“黄豆”、“黄米”、“黄皮肤”,都视作中华文明落后的印记。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历史宿命论,是一种极端的逆向民族主义,就差喊出“让外国人再殖民三百年”了。
然而,《河殇》这股思潮,迅速弥漫在整个华人世界当中,成为了后来所有逆向民族主义的祖师爷。
所幸的是,八九十年代最凶险的政治风波,中国熬过来了,没有被击垮。
但这些思想还是让整整一代人中,不少人都被带歪了,天生就觉得外国人比中国人更高等,还误以为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殊不知价值观大多数都是后天塑造的。
随着两千年以后网络的普及,他们又以线上为阵地,争夺了舆论话语权。
这些河殇派换了个名头,还给自己贴个了“我们才是真的爱国”的名号,但不外乎还是那些思想,毫无进步,甭管什么事情让他们来评价,他们七拐八拐都要拐到“中国人不如外国人”这个论点上去。
在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力与日俱增的时候,中国在舆论场的地位却和国力严重不匹配。
但所幸的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一批实事求是,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人也站了出来,开始为中国说话。
张召忠将军化身为战忽局局座,金灿荣C位出道成政委,丁一凡、张维为、马前卒、袁岚峰等都开始在网上展露风采。
相比初高中文化或者降分录取大学的很多公知而言,他们都有自己专业范围内的知识,水平扎实,不会有太多常识性错误。
最重要的,工业党的立场是民族和国家,理想是浩瀚的星辰大海。
他们不像公知一样消费大众焦虑,也没有“我只在乎小民尊严”的幼稚,而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真正的建设性意见,而且愿意和大众科普。
一来一去,轮番交锋后,公知党们当然就原形毕露,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但可惜的是,他们那一批人影响的那代人中,有一些人已经过了塑造价值观的年代,思想转不过来了,对中国的进步也视而不见,还活在中国不如外国的阶段。
而他们又牢牢掌控着某些具体的职务。
比起朝气蓬勃的80、90后00后,他们在处理问题,尤其是涉及外国人问题的时候,天然心理就矮了人家一头,做起事来如何不束手束脚,让人诟病?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人,逼他们改正当然是必要的,但根除思想上的顽疾也是当务之急。
《战狼2》和《流浪地球》固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敢于在荧幕上树立“中国人能打赢外国人”、“中国人能拯救全世界”这样的观念,就是思想上的一大飞跃。
以后,文艺界还会有更多客观讲述中国进步,讲述中华文明优点的作品井喷泉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方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来做成这件事,我们同样要花很久才能改过来。
等到新生代的那一批有自信有能力的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之后,这种事情自然会烟消云散。
很多人误以为东方文明现在对西方文明还是劣势的,但其实,光东亚圈子这边的几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加起来,就已经和西方文明整体不相上下了,改朝换代的日子不会远了。
等到哪一天,如果中国为首的东方文明实力全面碾压西方文明了,我们有兴趣,也可以花点钱,去欧美国家奖励一批知识分子做学问,提一提新的概念。
比如什么“海殇派”啊,还可以拍个纪录片啊,就叫什么《海殇:帝国的劣根性》啊。
让他们在给年轻人讲故事的时候不断在故事里偷偷质疑:
为什么欧洲国家那么多海盗,英国女王还给海盗发私掠许可证,官方背书?这是否说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天生只懂掠夺和盘剥,从来不事生产,具有劣根性?
为什么欧罗巴和美洲大陆祖先都是一个个贪婪的盗贼?用武器和病毒屠杀对他们友好的美洲土著,还设立“感恩节”猫哭耗子,是否说明欧美文明是天然的杀人犯?
这是不是人种问题?民族问题?
让他们对着年轻人上课的时候上到一半突然轮番感慨:
“上帝不再眷顾亚伯拉罕”;
“深蓝的海洋文明……终究只能让人走向深渊”;
“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海洋里流淌出来”;
“这片大陆不能再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权”;
“罪恶和惩罚必将降临在美利坚”。
学术著作也要跟上,什么《论西方的衰亡》《丑陋的美国人》《帝国的落日》都安排了,读来男默女泪。
到时候,你看还会有对着外国人直不起腰来的国人吗?
在线下载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