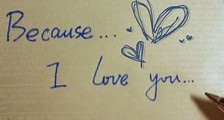作者: 虚声
来源:虚声(公众号ID:lxlong20)
已获授权转载
因为这轮选举会触及到伊朗体制的终极考验,同时也会暴露出宗教国家面对世俗冲击的世纪困局,也是验证立体史观的一个绝佳视角。早在5月25号,伊朗内政部公布了伊朗宪法监督委员会认可的7名候选人大名单。赛义德·贾里里,曾任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保守派。穆赫辛·雷扎伊,现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曾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保守派。阿里礼萨·扎卡尼,现任伊朗议会研究中心主任;保守派。阿卜杜尔纳赛尔·赫马蒂,伊朗中央银行行长;无派系。

这个名单一出来就引发巨大争议。因为很明显,它是为莱西量身定做的。
此前呼声很高的清流派前总统内贾德、保守派拉里贾尼、改革派的贾汉格里直接被排除在外。原因在于他们支持率较高,可能威胁到莱西的选情。清流派的前总统内贾德,第一个表示不服。他当时就表态,不愿意参与投票,抗议。不服归不服,虽然他是伊朗前总统,且影响力巨大,但对宪法监督委员会没有丝毫作用。改革派的现总统鲁哈尼(任期满,不得继续参选)致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恢复一些参选人的竞选资格。鲁哈尼是这样说的,“选举的核心是竞争。如果你把它拿走,它就变成了一具尸体。”这话意思再明显不过,大名单七人,搞了五个保守派出来,另外两个非保守派候选人还没有竞争力。虽然贵为现任总统,但面对宪法监督委员会,鲁哈尼和内贾德一样无能为力。这里顺便说一下,作为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能牢牢掌控伊朗这些年,主要就是依赖这个宪法监督委员会。这是极富有伊朗特色的组织。要讲明白这个观点,就得从很久之前说起。下面这段有不少干货,但读起来可能有点烧脑,不喜欢可以跳过。大凡中东国家,都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小国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都有说不完的历史。伊朗更是如此。早在秦帝国统一天下之前,伊朗高原上的波斯帝国已经横扫中东,巅峰时期领土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不论是亚历山大东征还是蒙古人西征,都要对伊朗高原用兵。加上近代又发现了大量石油,英、美、苏(俄)几个超级大国围绕伊朗斗得不可开交。中国壮大之后,也在伊朗打造自己的布局,逐渐成为一方棋手。可以说伊朗高原自古就是强者的角斗场,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的山地文明。伊朗历史非常漫长且复杂,要讲明白颇为不易。但通过立体史观视角可以简化,只需要记住两个民族和两个宗教就行了。雅利安人是世界三大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早期活跃于中亚大草原。大约在中国的商周时代,雅利安人南下,灭了四大古文明中除华夏文明之外的三个(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顺便征服伊朗高原。
因为有这段辉煌,后世人寻找祖宗时都会想起雅利安人。希特勒就认为雅利安人是日耳曼人的祖先,希望日耳曼人如雅利安人一样征服世界。而且二战期间,第三帝国的触角一度延伸到伊朗。巴列维一世,就因为站队失败,被迫流亡他乡。
雅利安人在南亚创建了印度教,促使印度文明诞生。至今印度底层人喜欢幻想来世变成神牛,就是拜印度教所赐。雅利安人在伊朗高原创建了拜火教,促成古波斯文明诞生。也就是说伊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源自于拜火教。但拜火教在中东远没有印度教在南亚(没有天敌)那么幸运,遭遇到中东土著闪米特人创建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强力狙击。决定性的转折源自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从波斯湾南岸(沙特)崛起,被伊斯兰思想武装起来的阿拉伯帝国征服了伊朗高原。此后大约2个世纪,伊斯兰教在伊朗高原取代拜火教,成为伊朗高原的精神支柱。波斯文由楔形改成阿拉伯的蝌蚪形。很多阿拉伯语词汇进入波斯语,约占波斯语的60%。也就是说大致以中国唐朝为节点,唐朝之前的伊朗高原是雅利安人创建的波斯文明;唐之后的伊朗高原是阿拉伯人创建的伊斯兰文明。阿拉伯人以逊尼派为正统,波斯人奉什叶派为旗帜。尤其是阿拉伯帝国衰亡之后,波斯人复国,但并没有复波斯文明,而是以什叶派旗手自居。所以如今中东格局中,有什叶派博弈的地方就有伊朗,有逊尼派博弈的地方就有沙特,于是就形成沙特和伊朗在中东隔着波斯湾海峡对峙的基本格局。
传统意义上的波斯,不仅局限于伊朗高原,统治范围长时间包括中亚以及阿富汗。以什叶派旗手自居的波斯命途多舛,遭遇过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摧残。到了近代,波斯人建立的萨法维帝国更是遭遇灾难性打击。沙俄从北向南,把萨法维帝国的中亚部分领土(阿塞拜疆、库土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拿走;英国从东(英属印度)向西,拿走了阿富汗部分地区。
列强之所以对波斯垂涎欲滴,根源就在于石油。近代中东第一口油井所在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整个巴库都是一座石油城),早期就属于萨法维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更是为争夺萨法维帝国的石油大打出手,终于把萨法维帝国搞解体,以什叶派旗手自居的波斯帝国就此进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巴列维王朝。眼见传统的伊斯兰帝国行不通了,巴列维一世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建立世俗化王朝。为凝聚民心,以复兴伟大的波斯文明(实际上波斯文明也是宗教文明)为旗号。由于希特勒的野心,又由于巴列维一世想利用德国抵挡仇敌英国和俄罗斯,伊朗和纳粹德国走到了一起。但是在中东,纳粹德国的力量显然比不上英国和苏联。1941年夏,同盟国军队开入伊朗。因为站队失误,巴列维一世被迫登船逃难,临走前把一块波斯泥土装进一个小包,塞到自己的口袋;几年之后在南非驾鹤西去。二战之后,巴列维二世紧抱美国大腿,大张旗鼓地搞世俗化。巴列维王国的各项经济指标蹭蹭上窜,在世俗化道路上狂奔。1971年,巴列维二世请了20位国王、26位王室成员、14个国家的总统和3个国家的副总统、3位总理,到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并且在居鲁士大帝(波斯帝国创立者)陵前发表演讲。那个极尽奢华的庆典,既是伊朗世俗化的巅峰,也是末日。
伊朗经济发展的同时,腐败指数也是蹭蹭上窜,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于是教士集团在霍梅尼的带领下发动伊斯兰革命,于1979年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历史上,就巴列维王朝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为特殊。巴列维王朝虽然是王国,却是世俗化政权,在伊朗历史上独一无二,在整个中东历史上也屈指可数;它虽然被推翻了,但至今依然影响着每一位伊朗总统和改革者的命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虽然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却大规模搞选举。当然伊朗的选举,和普通的民主选举不同,它是极富伊朗特色的宗教民主。一般来说,宗教和民主是对立的。但在当今伊朗,宗教民主是对立统一体。那么霍梅尼是如何把宗教和民主对立统一起来的呢?确切说就是设置了最高领袖这样一个职位,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权力,在幕后操控一切,且没有任期限制。为体现民主,霍梅尼搞出一个叫“专家会议”的机构,负责选举并监督最高领袖,必要时甚至可将最高领袖罢免。伊朗宪法规定,专家会议的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任期固定为8年。他们类似全国人民代表。议员们看似权力很大,但成为议员候选人,必须经过“宪法监督委员会”批准。如果说“专家会议”体现了伊朗政体中民主的一面,那么“宪法监护委员会”则体现了伊朗政体中宗教的一面,保证了教士阶层的特权。伊朗宪法规定,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名成员构成,一半以上必须由宗教学者出任,且由最高领袖指定。如此一来,宪法监护委员会就成了最高领袖的支持者(反对最高领袖的人无法进入专家会议),负责监督审查伊朗所有议员、总统等重要人物的资格背景。
所以这次伊朗大选,不论前总统内贾德,还是现总统鲁哈尼,尽管对“宪法监督委员会”拟定的候选名单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因为人家成员只忠于最高领袖。
费了这么大劲,总算把伊朗特色选举搞清楚了。这里再强调一下,伊朗是宗教民主。只不过是宗教在前,民主在后。人类文明史上看,宗教民主也算是一种尝试。那么为什么说这次伊朗13届大选是终极考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伊朗这次选举的内涵。毫无疑问,这届伊朗大选,哈梅内伊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莱西推上去。老铁们或许会纳闷,名单中有五个强硬的保守派,难道不担心分流选票么?理论上来说当然存在这种情况。但既然这是富有伊朗特色的选举,那么这种可能性就能轻而易举地排除。投票之前,保守派的贾里里、扎卡尼宣布退选,转而支持莱西;就连唯一的改革派候选人迈赫尔·阿里扎德也宣布退选。莱西当选,也就是走一个流程。当然最后陪莱西走完流程的,是赫马蒂。此人是一个精明的银行家,是那种在宗教国家最不受待见的角色、无论和谁搞选举都会输,自然也就无法对莱西造成任何威胁。哈梅内伊这么保莱西,正好体现出伊朗大选的三大内涵。莱西是强硬的保守派,但并不是第一次参选总统。早在2017年,他就以保守派代表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改革派的鲁哈尼。当时的鲁哈尼势如破竹,原因在于他在2015年和奥巴马谈妥了“伊朗核协议”,给贫弱的伊朗经济争取到难得的喘息之机。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撕毁了“伊朗核协议”,让改革派在伊朗的威信急剧下跌,保守派获得的支持率持续走高。
拜登上台之后推翻了特朗普的政策,要重返“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改革派的选情原本是巨大利好。但是,哈梅内伊掌握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直接否决了改革派大将(副总统贾汉格里)的选举资格。哈梅内伊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怎么好。这次大选不仅是选总统,也可能是选最高领袖接班人。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晚年,哈梅内伊就是从伊朗总统位置上接班的。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中意的保守派扶上台,把所有能威胁莱西的候选人排除。
在立体史观的大历史周期中,对于一个新诞生的体制(宗教民主)而言,比最高领袖换人更重要的是,开国功勋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时容易发生震荡。最典型的就是苏联,开国功勋集团最后的大佬勃列日涅夫(在卫国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退出之后,战后出身的戈尔巴乔夫就把帝国玩坏了。以美国而论,开国功勋集团退隐之后,南北战争就在酝酿。以中国历史而论,汉、唐、明这些大一统王朝,开国功勋集团之后都发生了剧烈震荡。其实过渡最好的是现代中国。在第一代领导人集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设计师,带领中国搞改革开放,完成了历史使命。伊朗以色列革命到现在已经40多年。开国功勋集团的骨干,正随着哈梅内伊的老去而退出历史舞台。哈梅内伊这么多年,并没有完成伊朗版改革开放。作为开国功勋集团最后的巨头,哈梅内伊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人继承自己的位置,确保伊朗不会被和平演变。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梅内伊一定要选择一个保守派,不是莱西,也会是其他人。所以这次伊朗大选,首先要排除改革派(贾汉格里)和清流(内贾德)巨头参选。但摆在哈梅内伊或整个伊朗保守派面前的,并不是让谁参选、或谁胜选;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选票。欧美媒体经常说伊朗是独裁国家,但其实选票对伊朗和欧美国家一样重要。作为建立在宗教民主基础上的伊朗共和国,根基就是投票。回到40多年前,伊朗人之所以认可霍梅尼发动的伊斯兰革命、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巴列维王朝,主要因素有两个。简单来说,当年伊朗人之所以接受伊斯兰共和国,是因为其提倡的宗教民主制,看起来既兼顾了伊斯兰传统,也符合时代大潮。
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认为“选举是一种宗教义务”,并在遗嘱中特意写道,“在某些情况下,不参加选举可能是一种重大罪行”,那些没有投票的人“将被安拉追究责任”。
当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阐述伊朗的“宗教民主”时说,这个政权赖以生存的“秘密”是它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那些呼吁抵制选举的人是在“执行敌人的意愿”,并强调如果“削弱宗教和民主,伊斯兰和伊朗将受到伤害”。换句话说,如果伊朗人抵制投票,伊朗政权将失去合法性。为什么在得知自己被排除候选人时,内贾德会说自己不去投票?这是一种威胁。因为内贾德代表的清流在伊朗人气颇高,他抵制投票,就会降低大选投票率。为什么鲁哈尼对哈梅内伊说,“选举的核心是竞争。如果你把它拿走,它就变成了一具尸体。”就是要告诉哈梅内伊,这么玩(把人气高的候选人排除)会降低伊朗人的投票热情。新闻公布的民调显示,这届选举伊朗人的投票热情确实不高。对伊朗精英阶层(相当一部分是改革派)来说,反正结果已经注定,投票与否都无所谓。为了这次大选,哈梅内伊亲自督促伊朗人去投票。他在克尔曼沙赫的代表在星期五的祈祷布道中说,“在选举中投票就是投票支持伊斯兰教、最高领袖的统治和烈士的鲜血”。如果得票率过低,莱西不论在伊朗总统位置上、还是将来接替哈梅内伊成为第三任最高领袖;都会长期面临合法性遭到质疑的尴尬。如此便会给伊朗政局增加动荡因素。但总体而言,伊朗各界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能重视投票率,相比中东其他国家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是由于选票这样一个特殊的考验存在,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总统,都成为了改革派,并且走向其政治对立面。比如拉夫桑贾尼总统,他是霍梅尼的左膀右臂、哈梅内伊的战友;但他上任之后主张跟西方缓和关系,搞自由化,发展经济;最后跟哈梅内伊闹翻。比如哈塔米总统。此君是霍梅尼的孙女婿,上任之后却是更加明显的自由派;跟哈梅内伊闹翻。比如草根出身的内贾德,是哈梅内伊一手提拔的,最后和哈梅内伊闹翻得更彻底。
要发展经济,就要想办法突破西方制裁,和西方搞好关系,不知不觉就成了所谓的改革派。正因如此,哈梅内伊一定要保证他的继任者是保守派(莱西),才能保持伊斯兰共和国不变色。所以才有这届大选,其他选手都是莱西的陪跑者的现象。这牵扯到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第四个层次,也就是文明周期的更迭。看过我书的朋友都了解,立体史观一共就四个层次,高层次的历史周期必然带动低层次历史周期运转。两千多年前,农耕文明到来时,地球村迎来体制、经济、政治、军事大洗牌。中华帝国占据历史先机,长期处于世界第一集团。纵观人类文明史,17世纪工业文明爆发,地球村再次迎来体制、经济、政治、军事大洗牌,很多帝国(法兰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大清帝国)被冲垮。那些勇于改变的国家,如基督教世界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占据世界先机。那些没有占据工业文明先机,但奋发图强的国家,如华夏文明圈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也都取得非常可观的发展。那些固守传统不肯改变的国家,如伊斯兰世界的那么多国家,发展并不乐观。因为伊斯兰意识形态,源自于游牧文明周期,不适宜指导工业文明的发展。这就是所有伊斯兰国家,没有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原因。即便波斯湾南岸那些富裕流油的石油王国,终究也就是靠老天爷赏饭(石油)吃。这里的世纪困局是指,企图以工业文明之前的意识形态指导工业化进程。相比波斯湾南岸那些石油王国,伊朗在体制上已经做诸多改进。但是伊朗固守宗教民主这个思维模式,其实还是固守伊斯兰的意识形态。所以便陷入了世纪困局。从这个角度看,莱西不论是作为伊朗总统,还是将来成为最高领袖,都面临着及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局面,担子非常重。
在线下载列表